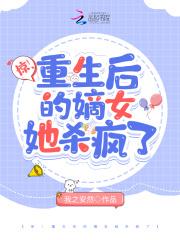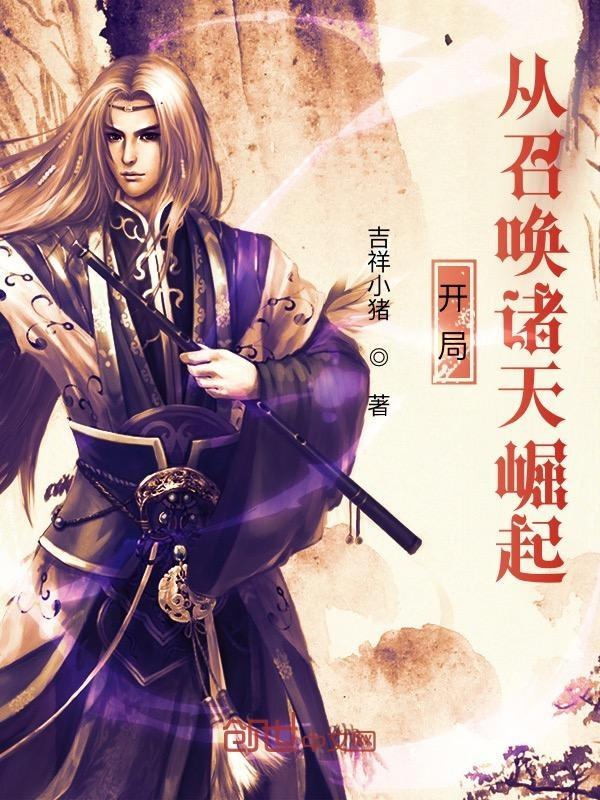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状元郎 > 第二百七十五章 阅卷(第1页)
第二百七十五章 阅卷(第1页)
黄昏时分,云板敲响,大宗师沉声道:“收卷!”
各个考棚的值场官吏闻命,立即纷纷下令道:“停笔,交卷!”
这会儿绝大部分考生都已经答完卷了,便撕去一半浮票收好,起身鱼贯交卷。
也有个别。。。
夜阑人静,烛火摇曳。苏录伏案于书斋之中,指尖微凉,墨香氤氲。窗外秋风扫过庭院,枯叶簌簌作响,仿佛天地间只剩他一人独对孤灯。桌上摊开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已被翻得页角卷起,朱笔批注密密麻麻,如蛛网织就心绪。
明日便是乡试首场,三场连考九日,食宿皆在贡院号舍之中。今夜是他最后一段自由时光,却不敢有半分懈怠。他深知,这一战,不只是为功名,更是为一家老小的生计、为亡父未竟之志、为那自幼便压在肩头的“神童”之名。
他轻轻摩挲着袖中一枚铜钱??那是母亲临行前塞进他衣袋的,说是祖上传下的压惊钱,能护读书人平安登科。铜锈斑驳,边缘已磨得光滑,像极了这些年家中省吃俭用攒下的每一分银钱。
“公子,该歇了。”老仆苏福提着灯笼站在门外,声音低沉而关切。
“再看一盏茶功夫。”苏录头也不抬,笔尖轻点稿纸,默诵昨日拟写的破题:“圣人之道,如日中天……”
话音未落,忽闻远处鼓楼传来三更鼓声,咚??咚??咚??,沉闷如雷,震得窗棂微颤。那一瞬,苏录心头猛然一紧,似有所悟,又似被什么无形之物攫住。他缓缓放下笔,闭目凝神,脑海中浮现出三年前父亲病榻前的最后一句话:
“录儿,文章不在巧,在诚;取士不在文,在心。”
彼时他尚年少,不解其意,只知日夜苦读八股范文,模仿名家腔调,力求字字合矩、句句合规。可如今回想起来,那些堆砌辞藻、空洞无物的文章,真能承载圣贤之道?真能让主考官动容?
他睁开眼,目光落在案上那份誊抄整齐的策论草稿上。题目是《论井田复可行否》,这是近十年来常考之题,坊间已有无数范文流传。他的初稿引经据典,条理清晰,甚至引用了欧阳修、司马光的观点加以佐证,结构工整得如同匠人雕琢的木器。
可此刻再看,却觉满纸虚言,毫无生气。
他忽然起身,从箱底取出一本破旧手札,封皮泛黄,题曰《先君杂记》。这是父亲生前随手所录的读书心得,并非专著,也从未示人。翻开一页,只见蝇头小楷写道:
“今人谈井田,皆据《孟子》‘方里而井’之说,然周制实因地而异,非一刀切之法。后世欲复井田者,不察民情、不顾时势,徒执古礼以绳今世,岂非刻舟求剑?治国如医病,贵在辨证施治,岂可但诵药方而不问病人寒热虚实?”
苏录心头一震,如遭雷击。
原来如此!
他一直以为八股只是应试工具,只需按格式填词造句即可。可真正的文章之道,是在规矩之中见性情,在限制之内显见识。若一味模仿套路,纵使辞采飞扬,也不过是一具披着儒袍的空壳。
他当即撕去原稿,重铺素纸,提笔写道:
“臣闻井田之制,兴于三代,废于秦汉。后世儒者多叹息之,以为王道之基堕矣。然臣窃观古今之势,地力不同,户口有增,风俗各异,岂可泥古而强复乎?夫王者之政,贵因时制宜,非必尽循旧章。譬如农夫耕田,沃土宜稻,瘠壤种粟,岂可强令天下皆种嘉禾?故井田之精神,在均贫富、安黎庶,而不在于画地为井、析田为公。若今之世,能行轻徭薄赋、抑兼并、广屯垦,则虽无井田之形,而有井田之实矣……”
写至此处,东方已现鱼肚白。晨露沾湿窗纸,鸡鸣破晓。苏录搁笔长叹,只觉胸中块垒尽消,仿佛多年困顿终于寻得出口。
苏福推门进来,见公子双眼通红却神采奕奕,桌上散落着撕毁的稿纸与新写的篇章,不禁笑道:“看来昨夜得了真章。”
苏录点头:“以往作文,如戴镣铐跳舞;今朝方知,镣铐之中亦可舞出真意。”
二人简单梳洗,背起考篮出门。天边朝霞如血,映照京城街巷。街道两侧已有不少考生结伴而行,或神色紧张,或故作镇定。贡院门前早已排成长龙,差役持棍巡视,搜检入场。
轮到苏录时,一名胖脸差役伸手在他袖中一掏,竟摸出一块干粮。
“带食物进场?”差役眉头一皱,“按规定要罚!”
苏录连忙解释:“大人明鉴,此乃家母所备,恐我在号舍饿着……绝无夹带舞弊之意。”
那差役正欲发作,忽听旁边一位青袍官员淡淡道:“让他进去吧。”
声音不高,却自有威严。众人侧目,只见此人约莫五十上下,面容清癯,眼神锐利如鹰,胸前补子绣着云雁纹样??乃是监察御史一类的京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