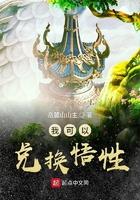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状元郎 > 第二百七十九章 院案首(第1页)
第二百七十九章 院案首(第1页)
翌日,所有考卷批阅完毕,拟录取的五十员额也出来了,并排定了名次。
虽然后面还有一场面试,但已经不会再有变数了。所以那其实是大宗师用来跟新科秀才见面,互相了解,增进感情的。
此外,尽管五十名。。。
苏录在号舍中静坐良久,耳畔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,夹杂着远处考生咳嗽、叹息乃至低声呻吟的声音。贡院之内,万籁俱寂却又暗流涌动,仿佛一座巨大的熔炉,将千余名士子的理想、焦虑与才学一同锻压成文。他闭目调息片刻,待心神安定,方才提笔写下第一场首题《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》。
此题他曾于模拟试中精研细作,然此时身处真实考场,心境迥异。前番挥毫尚带意气,今则须字字如履薄冰,既要展露胸中丘壑,又不可过于锋芒外露,以免触怒考官忌讳。他深吸一口气,落笔破题:
“君子所务者本,非枝叶也;本既立,则道自生焉。”
八字起势沉稳,承题继以“盖天下之道无穷,而所以贯之者惟一本”,语出正统,合乎程朱理路。然至起讲处,他略作停顿,终是依原思入理,引《易》曰“大哉乾元,万物资始”,以天地生物之仁为根,推及人心中一点恻隐之端,谓孝悌乃仁之初发,而仁实为政教之根本。其言虽未明斥时弊,然已隐隐指向朝廷重法轻德、苛敛百姓之失。
写至此,窗外忽有雨声淅沥而下,敲打瓦檐如碎玉纷飞。号舍漏雨,湿气渐重,苏录袖角微潮,却不肯稍动避让,唯恐扰乱文思。他咬牙续写入手、起股,层层递进,终以“故圣王治世,不求速效于民财,而在培植斯民之心”作结,全文三百四十七字,无一赘语,气脉贯通,宛如清泉出谷。
搁笔之际,天色已暮。他揉了揉酸胀的手腕,就着冷茶啃下半块芝麻饼,仰头望着从屋檐滴落的雨水,在泥地上溅起一朵朵浑浊的小花。夜风穿廊而过,带来阵阵寒意,他紧了紧单薄的青衫,心中却燃着一团火??这一篇,他对得起十年苦读。
次日清晨,雨歇云开,第二场论判诏诰之题发下。苏录展卷视之:论题为《汉宣帝所谓‘汉家自有制度’辨》,判题五道皆涉刑名钱谷,诏诰表科任选其二。他略一思忖,便先作论。
汉宣帝此语出自《汉书?元帝纪》,原为劝诫太子勿专务儒术而言,后世多解为务实拒虚之典范。然苏录以为不然。他援引董仲舒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之功,指出所谓“制度”,若无道德为体,终成权谋之具;并举王莽托周礼以篡汉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例,说明“制度”若失仁义为基,则反为乱阶。文末点睛:“故制度者,形也;仁政者,神也。有神无形,固不足行远;有形无神,尤易倾覆。”
此文立意高远,不随俗见,且辞锋锐利,几近讽喻当朝专务律例、忽视教化之弊。写毕,他自己亦觉心跳加快,知此论或招忌惮,然思及临行前母亲含泪之嘱、秦淮河畔立下的誓言,终不肯删改一字。
判词五道,他条分缕析,引《唐律疏议》《大明律》及近年案例,务求情法两尽。尤其一道关于里正私征羡余被判流徙之案,他主张“法贵持平,然情有可原”,建议减等发落,并陈“小吏迫于上官压力,不得不尔,根源在上不在下”,直指监察不力、责罚倒挂之弊。虽仅百余字,却如针砭病灶,令人凛然。
诏诰表三类中,他择“谢恩表”与“劝农诏”各一篇。前者措辞谦抑而不卑,后者广引《齐民要术》《吕氏乡约》,倡导兴修水利、推广良种,甚至提议设立“农师”一职,教导耕作新法。此类内容前所未见于科场文字,然其言有据,气象开阔,足见经世之志。
第三日,策问五道如期而至。苏录展卷细读,心头微震??题目竟与李怀瑾三人所拟极为相似!尤以第四题“科举能否增试算学、农政”最为相近。他不禁暗叹:莫非消息走漏?抑或本届主考果然重视实务?
无论缘由如何,他已胸有成竹。当下铺纸研墨,逐题作答。
首题江南水患,他详述太湖流域地势低洼、河道淤塞之状,主张“疏浚为主,筑堤为辅”,并建议仿宋代范仲淹“修圩田、通?港”之法,设专职河官,按年考核。更提出“以工代赈”,令流民参与治水,既除水患,又安民生。
第二题盐政,他痛陈官盐价贵、私盐横行之因,在于纲商垄断、层层加课,致使百姓宁冒死贩私也不愿购官盐。主张裁撤冗员、减轻课税、开放部分民间运销,同时严惩贪官污吏,“使盐利归于国,而非肥于吏”。
第三题卫所军屯,他直言洪武旧制早已崩坏,军官侵占屯田、役使军户如奴仆,战时则兵不成伍。主张清查屯田、还地于军,复设屯田御史巡察,并逐步推行募兵制,以精兵替代虚额。
第四题科举改革,正是他夙夜所思。他写道:“今取士但重诗赋帖括,致使聪明才智之士,毕生钻研虚文,不通钱谷,不识山川,一旦为官,茫然无措。”遂力主增设“明算”“明法”“明农”“明工”四科,每科设专门学校培养人才,考试录用,各司其职。并举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天文地理之学、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中百工技艺为例,强调“六艺之中,数与工皆圣人所重,岂可弃之如敝履?”
第五题流民问题,他剖析更深。指出赋役不均、豪强兼并、灾荒无赈为三大根源,建议清丈土地、均平赋税、限制兼并,并在各县设常平仓、义仓,遇灾即开仓济民。更请朝廷下诏罪己,减免重灾区三年赋税,以收民心。
五道策论洋洋洒洒近七千言,几乎耗尽全部精力。写到最后,他指尖颤抖,目光模糊,额头冷汗涔涔而下。然每一道答案,皆出自肺腑,字字带血,句句含情。他知道,这不是为了取悦谁,而是作为一个读书人,对这个摇摇欲坠的天下,所能尽的最后一份责任。
三日考毕,贡院钟鸣三响,大门缓缓开启。考生鱼贯而出,大多面色憔悴,步履蹒跚。苏录扶墙而起,双腿麻木如枯木,几乎不能行走。阿福早在门外守候多时,见他出来,连忙上前搀扶,眼中含泪:“公子,您瘦了一圈!”
苏录勉强一笑:“没事,活着出来了。”
回家路上,马车颠簸,他靠在车厢一角,昏昏欲睡。梦中似见母亲灯下缝衣,白发如霜;又见自己立于金殿之上,皇帝亲授状元袍带,百官俯首称贺。忽而风云骤变,严党爪牙群起攻之,弹劾其策论“谤讪朝政,妄议祖制”,龙颜震怒,圣旨下达:“苏录,革去功名,永不录用!”他跪地哭喊:“臣所言皆为民计,何罪之有?”无人回应,唯有雷声滚滚,天地漆黑……
惊醒时,已是深夜。他躺在自家床上,窗外月光如练。阿福端来热粥,轻声道:“老夫人熬了一宿,刚睡下。”
苏录默默接过碗,喝了几口,忽然问道:“这几日城里可有什么动静?听说别的考生出来后都在议论试题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