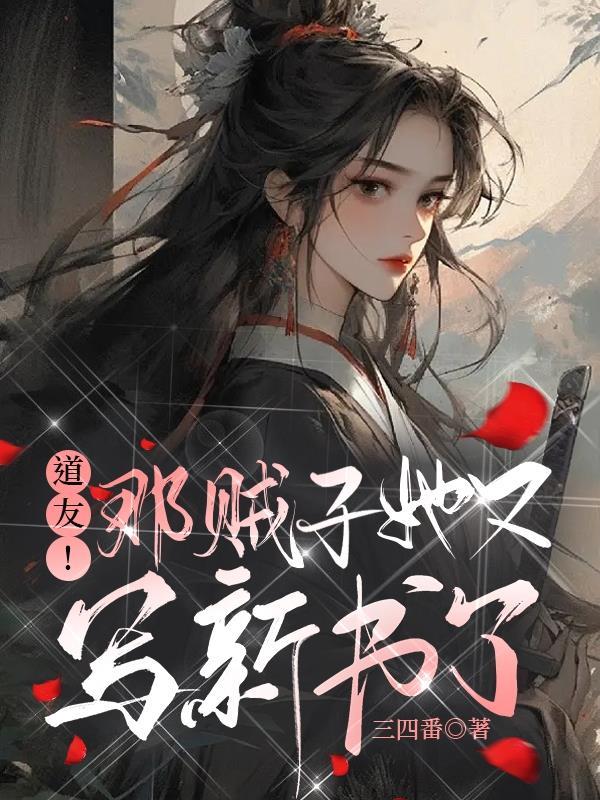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状元郎 > 第二百八十二章 书中自有黄金屋(第3页)
第二百八十二章 书中自有黄金屋(第3页)
“臣知道。”他抬头直视天颜,“但若因惧权贵而闭口,因畏祸患而藏策,则臣愧对‘状元’二字,更愧对陛下信任。”
皇帝凝视着他,忽然一笑:“好!果然是朕亲点的状元!有胆有识,不避锋芒!”
他拍案而起:“传旨:采纳苏录所奏四策,交由兵部、户部会同拟议细则。另,授苏录翰林修撰,兼经筵讲官,参与机务!”
退朝之后,张居正特意留下他,低声说道:“子衡,你今日之举,等于向整个权贵集团宣战。接下来的日子,必有无数明枪暗箭。你可后悔?”
苏录淡然一笑:“若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,那这顶状元帽,戴得又有何意义?”
张居正深深看他一眼,终是叹道:“你比我年轻时勇敢多了。”
风波并未就此平息。
半月后,御史台果然发难。一名言官上疏弹劾苏录“妄议国政,结党营私”,并指其《安邦策》中有“讥讽先帝旧制”之嫌,请求削籍为民。
奏疏呈上,朝野震动。
皇帝览毕,冷笑一声,提笔朱批:“苏录所言,皆为社稷计。尔等尸位素餐,不思报国,反妒贤嫉能,实为朝廷之耻!该御史上书不实,罚俸三月,闭门思过。”
消息传出,百官悚然。
自此,无人再敢轻易攻讦苏录。
而与此同时,他提出的改革逐步推行。屯田恢复,军饷发放,一批骁勇将士脱颖而出。北方边境局势渐稳,虏使再不敢轻易挑衅。
又逢中秋,苏录携婉儿登楼赏月。
她靠在他肩头,轻声道:“你说,我们以后的孩子,会不会也像你一样倔?”
他笑道:“希望他别像我这么傻,为一个女人放弃考试。”
“可我还是希望他像你。”她望着明月,“世上最难得的,不是一个聪明的男人,而是一个愿意为你对抗全世界的男人。”
他握紧她的手,没有说话。
远处,皇宫钟声悠悠传来,伴随着孩童背诵诗书的声音:
“……均赋税,简徭役,兴实学……”
那是《安邦策》的节选,已被收入蒙学课本。
他知道,自己的文字,正在一点点改变这个国家。
十年后。
苏录官至礼部侍郎,主持科举三次,选拔英才无数。他始终坚持一条原则:文章取士,首重真情实意。曾有一考生作文痛陈民间疾苦,泪洒试卷,苏录亲自提名为首,批语曰:“此子有心,胜于千言。”
婉儿身体渐愈,育有一子一女。每逢春闱放榜,她总会站在窗前,望着街上骑马游街的新科进士,笑着对孩子说:“你们父亲当年,也是这样风光回来的。”
而那只绣着“状元郎”的荷包,一直挂在床头,从未摘下。
某年冬,老仆整理旧物,在箱底发现一封泛黄信笺,乃是当年苏录写给婉儿的回诗残页:
>“此心如明月,夜夜照君台。
>纵隔千山雪,犹随一雁来。
>功名非我愿,相守是奇哉。
>若得长相伴,宁负紫金台。”
老仆捧着信纸老泪纵横,喃喃道:“少爷当年,真是把命都押上了啊……”
消息传到苏录耳中,他只是笑了笑,提笔在诗末添了一句:
**“幸不负卿,亦不负国。”**
窗外,梅花正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