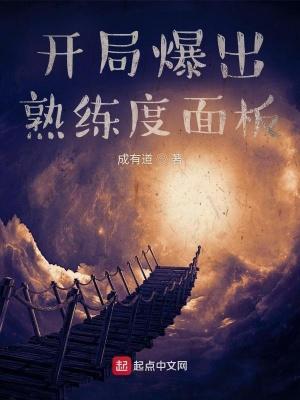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骊珠 > 8090(第43页)
8090(第43页)
被拦下来的文臣属官面面相觑。
“公主可别被覃主簿说动才是。”
“就是,覃主簿是尚书令的亲儿子,覃戎的亲侄子,他们覃家多方下注,自是希望公主能全力一搏,输了也有自家人兜底,可公主岂能背上拥兵自重,造反谋逆的罪名?”
几名武将在一旁竖起耳朵听他们的话风。
听了几句,横眉打断:
“说什么呢?这都什么时候了,不反难道真将赤骊军拱手交出去?”
杨舍人回过头,冷眼一扫,见是个络腮胡子的汉子,拂袖怒道:
“造反容易,可知反了之后要如何收场?公主身为女子,如果再得位不正,宗室子弟必将重蹈五王之乱,你们这些武夫倒是天天有仗可打,有功可立——打打打,你以为你们在前线吃的粮是天上掉下来的吗?那都是后方百姓勒紧裤腰带给你们送去的!”
这话听着不顺耳,又有军官帮腔道:
“老头,你说话可得凭良心,我们在前线哪一口粮是白吃你们的?没我们在前头浴血奋战,薛允早把你们屠了,还轮得到你们在这儿权衡利弊?”
“谁想打仗?谁家里没爹没娘?我看你们是怕自己被打成逆党,有损清名,想做墙头草了吧!”
王舍人:“我看你们才是想倚功欺主!”
文官嘴皮子利,武将脾气爆,纷争一挑起来,谁也不让谁,简直快要撸起袖子打起架来。
营外顷刻乱成一锅沸水。
大帐中的覃珣止住话头,朝外望去。
骊珠道:“不用担心,有裴照野在,他们不会真打起来的。”
覃珣听了这话,心中有微妙的情绪翻腾。
但很快,他又转过头,继续道:
“……我所知道的,就是这些了,公主是想从她身上下手?”
骊珠:“你觉得不可行?”
斟酌片刻,覃珣摇摇头道:
“不是不可行,而是人心如烟,不可琢磨,将三十万大军和公主的性命压在一个人的一念之间,太危险了。”
骊珠只拨弄着湿发,在炭盆前烤干,抿着唇没有言语。
那头乌黑长发逶迤垂地,刚沐浴过的潮红未完全从她面上褪去,垂眼时透出一种迎风浥露的娇美。
此刻的覃珣却无暇注意这种美丽。
他望着她的唇,她的手,生不出任何旖旎幻想。
这双唇口含天宪,这双手手握王爵,此时此刻,外面有无数人等着她的答案,有无数人的生死,取决于她一念之间。
没有等到骊珠确切的回答,覃珣不自觉拔高了声音:
“公主,就算要与父亲和二叔打得两败俱伤,难以应对北越,届时可以议和,可以用岁币来缓和战事,待南雍恢复元气,再征讨北越,总有办法可以解决!岂能因为不想牺牲将士,不愿消耗国力,就让我们这一路所做的努力都付之东流……”
“我要问你的问题,你已经给了我答案。”
骊珠放下梳子,抬眼看着他道:
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,覃玉晖,现在,你该退下了。”
她嗓音温和,然而语气却隐含着不容纠缠的决然。
覃珣背脊蓦然一僵。
她不是南迁至雒阳,一无所有的白板皇帝,他也不是与天子勠力以匡天下的权臣。
她会倾听他们每一个人的意见,但她不是世族选出来的傀儡。
没有人,可以做她的主。
她希望他能明白这一点。
在骊珠柔中带刚的注视下,覃珣眼睫微动,面上厉色逐渐消融。
很奇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