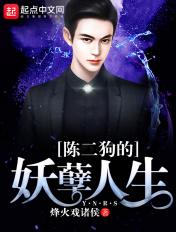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1977:开局相亲女儿国王 > 第七百五十七章 民企登台(第1页)
第七百五十七章 民企登台(第1页)
会客室中,李长河打量着邱达鑫。
现如今的邱达鑫年龄还不大,刚刚三十五岁,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。
“Victor先生,你好!”
邱达鑫主动打起了招呼,用的是粤语,还带一些客家口音。
。。。
运输机在爪哇海上空盘旋时,玛琳娜第一次呕吐了。不是因为颠簸,而是舷窗外那片熟悉的海岸线??雅加达湾的轮廓像一把锈钝的刀,割开了她记忆里最深的伤口。她曾在这里接妹妹放学,骑着破旧自行车穿过雨季泥泞的小路;也曾在这片码头边跪了一整夜,求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说出“她还能好起来”这句话。
舱内灯光昏暗,医疗队伪装成东南亚热带病防治小组,箱子里藏着改装过的神经扫描仪和微型信号中继器。苏珊娜设计的检测设备外壳印着WHO标志,内部却嵌入了能识别B11特异性β波衰减模式的算法芯片。阿米娜坐在角落,手指反复检查腰间的电磁脉冲发射器??它只能瘫痪电子锁三十秒,足够他们撬开一道门,也足以引来致命追捕。
“记住,”莉莉安最后一次叮嘱,“我们不是来打仗的。我们是来带人回家的。”
飞机降落在苏加诺-哈达机场外围一处废弃货运停机坪。印尼方面登记为“国际公共卫生援助行动”,由无国界医生组织背书,流程合规得近乎完美。但所有人都清楚,只要有人多问一句“为何携带如此高灵敏度脑电图设备”,整个计划就会崩塌。
玛琳娜换上护士制服,斗笠换成医用口罩,走在队伍最前。她的身份是本地协调员,负责引导团队前往西爪哇偏远村落开展义诊。车行两小时后,路线突然改变。原本通往山区的道路被临时封锁,官方理由是“山体滑坡”。可玛琳娜盯着窗外飞驰的棕榈树,低声说:“他们在清场。MK3站点今晚可能转移实验体。”
马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“回声协议”二级信道开启,通过短波电台向分散在全球的七处分站发送加密代码:**“拾荒者遇风,暂缓归巢。”**这意味着原定潜入时间推迟十二小时,同时激活备用接应网络。
夜幕降临,五人突击组转入地下行动。
他们藏身于雅加达老城区一栋废弃教堂地下室,墙皮剥落处露出上世纪殖民时期留下的拉丁铭文。李长河架起便携天线,尝试接入城市监控系统盲区。十分钟后,他调出一张模糊的卫星热力图:“西郊工业区有三处异常点,其中一处二十四小时内进出车辆全部遮蔽车牌,且夜间有冷藏货车频繁补给。”
“就是那里。”玛琳娜指着地图上一个红点,“我妹妹最后出现的地方,叫‘新希望康复中心’。名义上收治自闭症儿童,实际上……”她声音哽住,“我去过一次,走廊尽头有扇铁门,守卫不让进。但我听见里面传来哭声??不是疼痛的那种,是……像是有人拼命想说话,却发不出音。”
莉莉安翻开《证词集》,在空白页写下新名字:**黛薇?玛琳娜,16岁,印度尼西亚,数学天才,失语症,疑似B11-MK3阳性。**
她说:“从今天起,你妹妹不再是编号0。她是黛薇,会解微分方程,喜欢看星星,梦想去剑桥读书的女孩。”
众人静默。诺拉轻轻哼起那首童谣改编的暗语歌,节奏缓慢如摇篮曲:
>*“月亮下来走一走,*
>
>*看看哪个孩子不能开口。*
>
>*医生说他睡得太久,*
>
>*其实是针管偷走了梦的出口。”*
凌晨两点,行动开始。
伪装成维修工的突击队员先行抵达目标建筑外围。这是一栋伪装成工厂的三层混凝土结构,外墙爬满藤蔓,屋顶装有太阳能板,电力独立于市政电网。红外探测显示,地下至少还有两层,温度恒定在18℃,符合长期生物样本保存条件。
阿米娜带队从排水管道切入,顺利进入一楼锅炉房。通道狭窄潮湿,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与金属锈蚀混合的气味。她们贴墙前行,每一步都避开地板松动处发出的吱呀声。二楼是办公区,档案室门锁已被远程破解,李长河通过微型摄像头传回画面:成排文件柜标注着“项目曙光”“认知调控阶段III”“优育筛选名单”。
“找到了。”他压低声音,“MK3临床试验记录,涉及三百二十七名未成年人,年龄最小八岁,最大十七岁。干预方式统一为‘心理评估后注射认知稳定剂’,实际成分……正是B11衍生物。”
与此同时,玛琳娜与马克潜入地下一层。
这里是病房区。二十多个单间整齐排列,每个房间都有透明观察窗。孩子们躺在床上,头上戴着类似运动头带的装置,连接着墙壁上的黑色仪器。他们的双眼睁开,却无焦点地望着天花板,偶尔嘴唇微动,仿佛在默念什么。
“那是神经抑制环。”玛琳娜颤抖着说,“用来压制残余意识活动,防止他们产生反抗念头。”
她在第七号房停住脚步。
床上的女孩瘦得几乎脱形,脸颊凹陷,但眉眼依旧清晰。玛琳娜伸手触碰玻璃,泪水终于落下:“黛薇……姐姐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