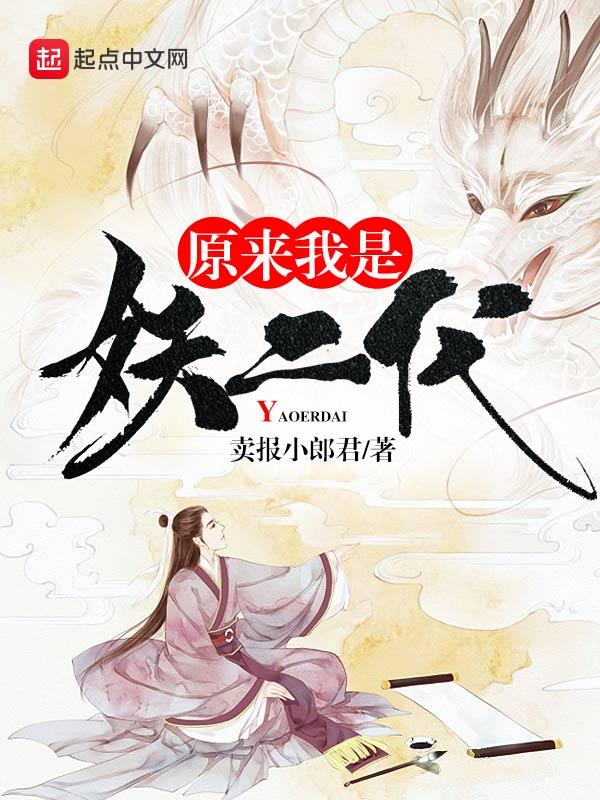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> 第663章首都之行的差池(第1页)
第663章首都之行的差池(第1页)
强忍着踹门催促的心思,陈着和宋时微在走廊上等了七八分钟,才终于把小秘书和小助理等了出来。
看了下时间,快8点50了。
在电梯的时候,陈着轻咳一声:“对时间的把握和重视,侧面也反映了工作作风。。。
哈尔滨的雪比兰州更冷,也更硬。江辰走出机场时,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,呼出的气息瞬间凝成白雾。他裹紧大衣,抬头望了一眼灰蒙蒙的天空??乌云压得很低,仿佛随时会塌下来。
“萤火列车”计划提交后,审批流程意外地顺利。或许是用户破亿带来的舆论热度,或许是教育部近期接连出台的情绪教育政策推动了社会认知的转变。但江辰知道,真正起作用的,是那一封封未曾寄出的家书、那一句句藏在心底十年的话、那个在牛粪堆旁终于开口说“我想洗澡”的女孩。
项目组只给了他七十二小时做实地调研:从哈尔滨出发,沿滨绥线南下,经牡丹江、绥芬河,再折返长春、沈阳,最后回到北京召开立项听证会。时间紧,任务重,可江辰却坚持要亲自走一遍这条贯穿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铁路线。他说:“如果‘萤火’要上车,就得听得见铁轨震动的声音。”
第一站选在哈尔滨东站附近的一所职业技校。这所学校九成以上学生来自下岗工人家庭,不少孩子初中毕业就进了厂,如今厂子没了,他们又被送回课堂,眼神里带着一种被时代甩出去又勉强捡回来的茫然。
江辰和团队提前联系了校长,以“情绪素养公益讲座”名义入校。教室不大,六十多个学生挤在一起,有人低头玩手机,有人趴在桌上睡觉。讲台上放着一台便携音响,是他特意带来的“声音博物馆”初代设备??一个能播放匿名倾诉录音的小盒子,外形像老式收音机。
开场没人鼓掌,也没人抬头。
江辰没说话,只是按下播放键。
一段女声缓缓响起:“我爸爸是炼钢厂的钳工,去年肺癌走了。临走前他攥着我的手说,对不起,没能给你买那双篮球鞋……我知道他不是不想,是厂里三年没发全工资。可我还是恨他,为什么不多活几年?为什么不早点去看病?现在我每天骑电动车送外卖,路过厂区大门都不敢看一眼。”
录音结束,教室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的水流声。
过了十几秒,后排一个戴耳钉的男生忽然站起来,嗓音发抖:“我爸也是钳工,也在等死。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。”他顿了顿,“但我从来没跟他说过我怕。”
没人笑他。
另一个扎马尾的女孩轻声接话:“我妈妈天天骂我是赔钱货,可她半夜偷偷哭,我都听见了。她一个人打三份工,就为了让我别像她那样嫁错人。”她说完,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,“这是我写给她的信,但我没敢给她。”
江辰走过去,接过信,念了出来:“妈,我不是不想上学,我是怕考不上让你失望。你累的时候,能不能也抱抱我?”
全班沉默。
然后,不知谁先开始,掌声一点点响了起来,先是稀疏,后来连成一片。
那天下午,他们临时增设了一个环节:每个人写下最想说却不敢说的话,投进“声音邮筒”。晚上十点,江辰坐在宾馆床上,一条条翻看扫描件。有写给逝去亲人的,有写给暗恋对象的,也有写给自己的。“我知道我不够好,但我不想再装作不在乎了。”??这是其中一句。
第二天清晨,他把部分匿名内容整理成音频,在校园广播站循环播放。第三天离校前,校长红着眼眶告诉他:“有两个学生主动去找心理老师谈话了。这在学校历史上,是第一次。”
列车继续前行。
牡丹江站外五十公里有个废弃矿区,曾是共和国最早的石墨产地之一。随着资源枯竭,青壮年纷纷外流,留下一群被称为“矿二代留守者”的中年人。他们在小镇边缘搭起板房,靠捡废铁、修农机维生,生活像被遗忘在时间之外。
江辰一行人租了辆面包车颠簸进去时,正赶上一场小规模冲突:两个男人在垃圾堆前对峙,一人挥舞着铁锹,吼着“你偷了我的铜线!”另一人则指着对方鼻子骂:“你老婆跟人跑了你知道吗?你还管什么铜线!”
调解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居委会大妈,穿着臃肿棉袄,手里拎着个保温杯。她一边劝架一边叹气:“这些人啊,心里憋得太久,一点火星就炸。”
晚上,他们在村部活动室办了一场“倾听夜”。没有PPT,没有专家讲座,只有几把椅子、一壶热茶、一台录音笔。
江辰问大家:“有没有哪句话,你们藏了一辈子,却始终没说出口?”
良久,一个满脸胡茬的男人开了口:“我想跟我爹道个歉。他死那年,我没回家奔丧。我说我要挣钱娶媳妇,结果媳妇跟别人跑了,钱也没挣着。”他低下头,“现在坟都找不到了。”
另一个人苦笑:“我老婆走的时候,我在井下加班。等我爬上来,人都凉了。她最后一句话是‘灯忘了关’。我一直觉得,她是想跟我说别的。”
屋子里渐渐安静下来,有人抹眼泪,有人抽烟,烟雾缭绕中,像一场迟来的祭奠。
临走时,那位居委会大妈拉着江辰的手说:“你们能不能留点东西?不是钱,也不是物资,就是……让人能把话说出来的地方。”
江辰点点头,当场决定将首列“萤火列车”的第一节车厢命名为“矿语者”,专门用于收集工业衰退带中的沉默故事,并邀请这些讲述者成为流动展览的志愿者。
第三站是绥芬河,边境小城,中俄贸易枢纽。这里的故事不一样??语言混杂,身份交错,情感也更为隐秘。
他们在一所中俄混血儿童学校驻点,发现许多孩子长期处于“双重失语”状态:在家里,父母用俄语争吵,他们听不懂;在学校,老师批评他们“不像中国人”,他们无从辩解。心理测评显示,超过四成学生存在轻度抑郁倾向,但当地没有懂双语的心理咨询师。
江辰想起次仁卓玛在那曲的做法,立刻召集团队设计了一场“梦境对话”实验。
他们请孩子们画出自己最常做的梦,然后由翻译人员转述给VR叙事设计师,制作成五分钟的双语音频故事。其中一个叫安娜的女孩,画了一扇红色木门,门外站着穿军大衣的外婆,手里提着一篮煮鸡蛋。
“我想跟她说话,可门打不开。”她说。
音频里,门开了。外婆走进来,用俄语哼起一首童谣,又用生涩的中文说:“安娜不怕,外婆给你留了酸黄瓜。”背景音是遥远的火车鸣笛和雪落屋顶的沙沙声。
播放那天,安娜听完后一句话没说,只是紧紧抱住江辰的胳膊,脸贴在他外套上,哭了十分钟。
当晚,团队收到一封来自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邮件。发件人是一位退休教师,自称是安娜的远房姨婆。她说:“我看到平台上传的照片,那是我姐姐最爱的围裙颜色。我以为她们早就搬走了,没想到还在这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