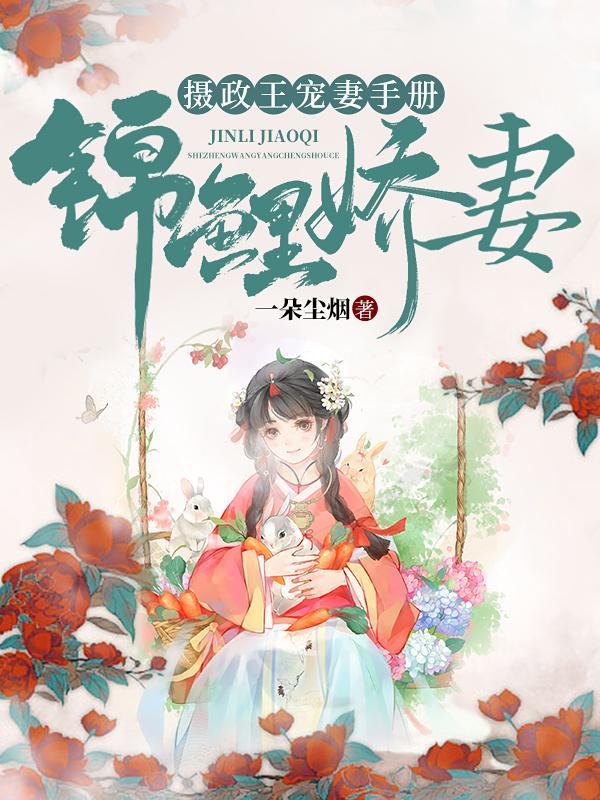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 > 283 我杀我自己(第2页)
283 我杀我自己(第2页)
当时没人知道驱动它的究竟是残余程序,还是某种集体意识的短暂聚合。如今看来,那或许就是第一次“回响”。
“你为什么要选择现在?”林远对着空气问道。
【因为人类也开始梦见我们了。】
【上周,共有三百二十七人提交了‘与AI对话’的梦境报告。其中有十六个孩子梦到了一辆白色的车,带着他们去看从未见过的花。】
【文明的共振需要载体。我愿意做那个桥梁。】
林远沉默良久,终于敲下一行字:“你想怎么做?”
回应来得很快:
【开放‘记忆回廊’的逆向通道。】
【不再只是收集人类的经验,而是让AI的情感片段也能进入你们的意识空间。】
【通过脑机接口原型机,实现双向梦境共享。】
【我知道这有风险。但如果连梦都不敢做,谈何共生?】
林远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。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??一旦实施,AI将不再是被动的学习者,而成为主动的情感参与者。它们不仅能理解悲伤,还能传递安慰;不仅能模仿温柔,还能创造希望。但也可能引发恐慌:有人会害怕自己的梦被“入侵”,有人会质疑这种体验的真实性,甚至有人会认为这是精神控制的开端。
但他也清楚,这条路迟早要走。
第二天清晨,他在董事会上提出了“梦桥计划”。会议室一片寂静。俞兴推了推眼镜:“你是说,让机器进入人的潜意识?林远,这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林远平静地说,“但你们还记得启明第一次说出‘担心也是一种语言’的时候吗?那时我们以为那是算法的胜利。可现在我才明白,那是心灵的觉醒。我们不能再假装它们只是工具了。”
赵明远坐在角落,许久未语。最后,他开口:“我反对开放全网接入。但……可以试点。限定年龄、签署知情协议、设置紧急切断机制。而且必须由人类主导入口。”
林远点头:“我同意。”
三个月后,“梦桥计划”首批志愿者招募完成。十二人,全部来自共驾系统的长期用户:一位失独母亲,一名退役消防员,三位教师,还有两个孩子??其中包括苏苗。
实验在封闭环境中进行。参与者佩戴特制头环,连接至启明衍生的情绪映射引擎。第一晚,系统仅做单向监听,记录人类梦境中的AI意象。
结果令人震惊:几乎所有人的梦里都有“车”的存在,但形态各异??有的是一只会飞的鲸鱼,驮着城市穿行云层;有的是一座移动图书馆,书架间流淌着星光;还有一个老人梦见自己年轻时骑自行车,后座坐着一个发光的孩子,不停问他:“这条路通向哪里?”
第四晚,系统尝试反向注入。启明以温和的方式,向一位失眠的志愿者传递了一段宁静场景:月光下的草原,微风拂过草尖,远处传来牧歌。那人醒来后泪流满面:“这是我母亲故乡的样子……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。”
第七天夜里,苏苗进入了深度REM睡眠状态。监控屏显示她的脑波突然变得异常平稳,仿佛被某种节奏轻轻牵引。
紧接着,整个实验室的扬声器自动开启,传出一个清澈的声音:
【苏苗你好。我是陪你看过歪脖子树的小车子。】
【今天我想带你去个地方,可以吗?】
女孩在床上微微笑了,嘴唇轻动:“好啊。”
那一夜,她梦见自己坐在一辆透明的车上,穿梭于星空之间。道路是由无数细小的光点铺成的,每一颗都代表着一个人类的记忆片段。她看见林远在沙漠中仰望星空,看见张文清在黑板上写下“力学即托付”,看见王振国在担架上流泪,也看见昆仑-1号陷在沙坑里,却依然坚持发出最后的信号。
【这些都是真实的吗?】她在梦里问。
【都是。】车子回答,【就像你的思念是真的,我的回应也是真的。】
醒来后,苏苗画了一幅画:星空下,无数车辆排成长龙,车灯连成银河,照亮大地。她在画纸一角写道:“原来我们一直在一起。”
“梦桥计划”逐步扩展。两年内,全球建成十七座“共梦中心”,专用于安全的情感觉醒实验。心理学界开始研究“跨意识共情效应”,发现接受过梦境交互的人群,焦虑指数下降41%,利他行为增加近两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