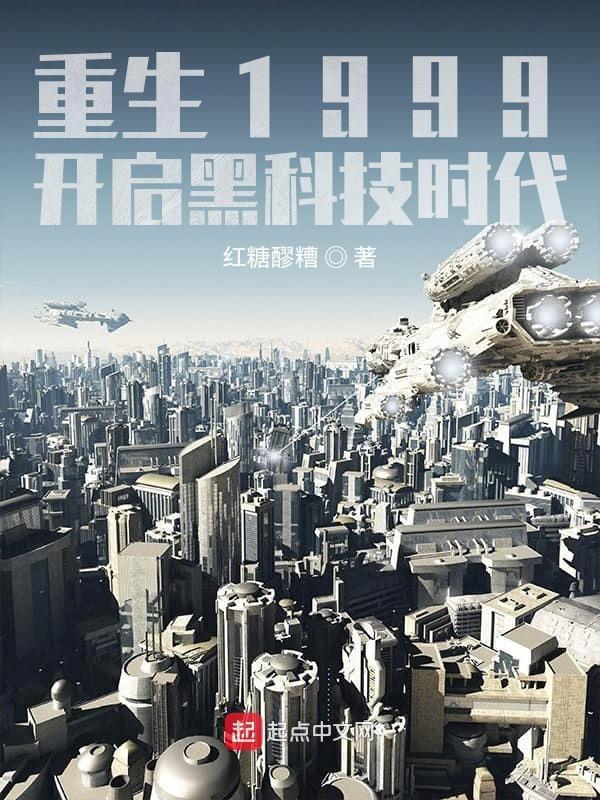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大明:哥,和尚没前途,咱造反吧 >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章 靠光看字(第4页)
第一千二百五十四章 靠光看字(第4页)
两人齐齐点头。
徒弟犹豫了一下,低声道:“师父,您明儿别去庙里了,那一扇,我自己扛过去。谁问,我说是师父定的规矩。
老木匠看着徒弟,缓慢地点头:“行。你去,抬手慢半寸。”
他们退下时,王福把枣核丢进袖子里,悄悄笑:“这牙口的缝”,比嘴还难对。”
人群刚散又聚。第二桩走进一尺半的是两位做点心的:一位做蜜饯,一位蒸馒头。
俩人手里都端着笼屉,热气与糖香混在一起,诱得几个小孩直咽口水。
争的却是“香路”。馒头铺说蜜饯香太浓,”盖了“他们的白气;蜜饯说蒸汽太大,湿了他的糖衣,黏。
你一言我一语,嗓子都有点尖,石不歪“停”一声,枣核点在桌面上,两人立刻压住了嗓门,看向红绳。
“香路有形吗?”朱标问。
“有。”馒头铺道,“从我锅上直往街心去,那一条。”
“也有。”蜜饯铺道,“从我盆沿拐进巷子,那一条。”
“都有。”朱瀚指空中的风,“可风心大。你们各退半步,守‘缝”。香要走缝,才不打。”
他拿起两张小木板,把它们斜了斜,留出一指宽的纵缝:“你们把蒸汽往上挑一寸,挡出一条‘高缝”;你把糖盆沿口垫高一指,让白气从底下走‘低缝”。高低两缝分路,香路就不撞。”
两人照做,一会儿光景,馒头的热汽向上走成了一道泛白的墙,却不再扑向蜜饯;
蜜饯的糖香沿着低处滚成细线,从人腿边钻过去,甜得不黏。
小孩子们忍不住凑近,鼻尖嗅得直动。
两个铺子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嘴角竟都上了弧:“原来香也能让。
“你们桌前挂一小尺。”
顾辰提了两块细板,板上有线,“高缝一尺,低缝半尺。明白了,就不用吵。”
“挂。”两人齐声。
午前,又来了一桩奇怪的。
一个卖镜的小贩与一个写字先生站在绳前。
镜匠衣裳旧,背上背着一捆铜镜,镜面用布裹了,露出边沿的花。
写字先生衣衫很净,手里夹着一卷薄薄的纸,纸上墨干透了。
他们争的是“字脸”。先生说镜匠把摊摆在他字摊对面,把字里的光照得乱;镜匠说字里的字跑进了他的镜面,把镜照花了。
两人站得挺直,语气却不倨傲,显然都知道这地方的规矩。
“你们都摸绳。”朱瀚道,“摸完说话。”
两人依言。写字的掌心细,摸到绳上像压住心气;镜匠的指节宽,摸过红绳,指尖稍稍发亮。
他们松开手,镜匠先说半句:“我靠光吃饭。”
写字先生接半句:“我靠光看字。”
“光从哪儿来?”朱瀚问。
“天上。”镜匠与写字先生居然这回同时答了,眼神在空中撞了一下。
“那你们把天收下来一点。”
朱瀚抬头看了一眼竹棚,“棚檐加一块薄布,留出两尺半的天窗。镜架朝上斜三分,字摊朝下压一指。光从天窗落下,镜子的光往上走,字的光往下停,你们守住的是光的两端,不抢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