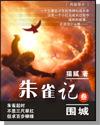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春色满棠 > 第429章 想去改变想去克服了(第1页)
第429章 想去改变想去克服了(第1页)
不知默默哭了多久,嬷嬷端着温水进来。
孟梁安听到声音,急忙抹干泪水。
嬷嬷将水在床边放下,拧干帕子,对孟梁安说:“县主,老奴来给世子擦身。”
她第一天强压下心头不舒服的感觉给沈东灼擦胸膛后,这两日都是叫嬷嬷来给沈东灼擦。
但今次,嬷嬷帕子要往沈东灼胸膛伸去时,孟梁安犹豫了下,突然说:“我来吧。”
嬷嬷愣了下。
她虽不知道孟梁安的过往,但在将军府也有好几年了,知道孟梁安厌恶与男人碰触,才不愿意亲手给世子。。。。。。
荒原之上,暮色四合,天边残阳如血,将大地染成一片金红。药车缓缓前行,车轮碾过碎石与枯草,发出细微的咯吱声,仿佛是这寂静天地间唯一的呼吸。孟梁安倚在车厢内,手中握着那本已翻得边缘磨损的笔记,指尖轻抚最后几行字迹,久久未动。
风从帘外灌入,吹起她鬓角几缕白发。她不避,只静静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影,像在等什么,又像只是在听。
忽然,远处传来马蹄急响,尘土飞扬。一道黑影自斜阳尽头疾驰而来,披风猎猎,背负长刀。来人勒马停于车前,翻身下马,单膝跪地,声音沉稳:“影针七队副统领沈砚,奉知棠姑娘之命,护送您前往陇西。”
孟梁安抬眸,目光温和却不容置疑:“我未曾召她派兵相随。”
“不是派兵。”沈砚抬头,脸上有一道旧疤横贯眉骨,“是求您别再一个人走。春棠馆如今已有三百弟子,巡医遍及十六州,可所有人都说??只要您还在路上,他们就敢去最险的地方。”
孟梁安怔了片刻,终是轻轻一笑,掀帘而出。晚风拂面,带着沙砾的粗粝与野艾的清香。她仰头望天,见第一颗星已然亮起,悬于苍穹之巅。
“那就一起走吧。”她说。
三日后,陇西疫区。
此处原为商路要道,因连年干旱,井水干涸,百姓饮用了山涧中泛紫的溪流后,陆续发病。症状初为皮肤溃烂,继而双目失明,最终神志涣散,口中反复低语:“花开彼岸,魂归故园。”??正是“招魂散”的余毒再现。
村落早已十室九空,屋舍倾颓,唯有村口一棵老槐树尚存,枝干扭曲如挣扎的人形,树皮上被人用刀刻满了“救”字。
孟梁安踏进村口时,正逢一场沙暴将至。黄云压境,天地昏暗。她却未避,立于槐树之下,伸手抚过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,指腹被粗糙树皮磨出血丝也不觉痛。
“这不是复发。”她低声说,“是有人在重新点燃火种。”
沈砚递上密报:三日前,一名游方道士进入此地,自称能引亡魂归家,以一碗“往生汤”换百姓家中孩童的生辰八字。已有十七户交出名录,名单皆指向八岁以下、体弱多病者。
“又是替身蛊的苗头。”孟梁安闭目,“他想再造一个容器,承载丙仲康残存的意识。”
“可丙仲康已死。”沈砚皱眉,“魂魄都随祭坛崩塌而散了。”
“执念不死。”她睁开眼,目光清冽如寒泉,“只要还有人相信‘死亡才是解脱’,他的思想就会借尸还魂。这一次,不过是换了件袈裟罢了。”
当夜,她在村中祠堂设诊台,燃起三炷安神香,挂出一盏蓝焰灯??与当年忘川祠那一盏,形制相同。
消息传开,残存村民陆续前来。有人抱着昏睡的孩子,有人扶着溃烂的老母,更多人眼中满是恐惧与期盼交织的光。
孟梁安逐一问诊,取脉、观舌、验瞳,动作极缓,却无半分错漏。她开出的药方简单至极:甘草、茯苓、灯心草,辅以井水(若无,则用雪融水替代),每日三服,静卧避风。
有人迟疑:“就这么简单?”
她点头:“病由心生,药亦治心。你们怕的不是毒,是孤独。以为死去便能团聚,所以甘愿赴死。可真正的归处,从来不在彼岸,而在彼此相守的此刻。”
那一夜,祠堂灯火未熄。她亲自煎药,一碗一碗端给病人,看着他们喝下,再轻抚孩童额头,哼起一支古老童谣。
子时刚过,沙暴骤停。
月光破云而出,洒在祠堂门前。忽有微响,众人回头,只见那株枯死多年的海棠盆栽,竟抽出一抹嫩芽,颤巍巍地向着灯光伸展。
“活了……”一位老妇喃喃落泪,“它闻到了药香。”
五日后,疫情渐稳,患儿陆续苏醒。那名游方道士也在山坳被捕,面具揭开时,竟是个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眼神空洞,口中仍呢喃着同一句话。
孟梁安亲自审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