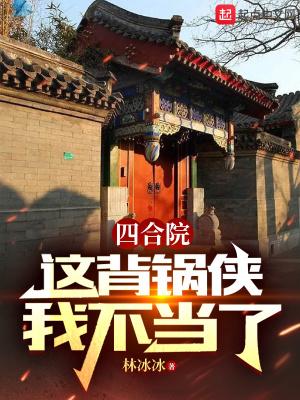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阿尔卑斯山的牧羊犬 > 第3章(第9页)
第3章(第9页)
艾瑞克继续往前移动,这边的阶梯陡峭看起来是直接沿着山壁雕刻而非石砖堆砌,每个石阶的尺寸皆不同,蜿蜒程度显然不是为人类所设计,透过火光,他缓慢远离石阶走向一座弯曲的拱桥,下方是漆黑的无尽深渊,周围的岩壁向上延伸而看不到尽头,他一时之间还无法领会自己正在每天看着的山里游走,这里被某种东西切割与排列成不规则的多边形立方体,几何构造相连建构出壮观又可怕的巨大建筑体,这完全不符合任何现代建筑学工程,他确信现在人类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建筑能与其相比拟,不同角度的多边体以一种违反常理的方式相互堆迭,艾瑞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用何种方式堆砌而成,随着距离缩短,他越是清楚看到这座可怕建筑的恐怖之处,乍看像是尖塔但又像是倒三角的金字塔,镶嵌在一起的石块往四面八方伸出怪异又恶心的触手。
拱桥尽头是巨大的六角蜂巢状的网状墙,绵延数百公尺甚至数公里,艾瑞克内心浮现出意思可怕的想法,要是这整座山都只是这座都市的掩护呢?
他按耐住心里的疯狂快步向前走,他可以听线呼啸的风声中带有无法理解的词汇,那些听上去像是拉丁语或是阿拉伯语,风与那些六角型蜂巢结构发出宏亮的共鸣,像是齐声高唱的远古歌谣。
穿过那些蜂巢结构体,另一侧是更加装阔的建筑,艾瑞克更接近那些高耸的建筑体,纵使那些高墙庞大,但艾瑞克确信占据整个视野的建筑只是冰山一脚,他继续往前走,他没看到贝格口中的光,那些建筑壁上的光点似乎是窗格子,但那些排列相当紧密而又毫无规则,艾瑞克的目光反复扫视那些建筑的构造,乍看之下是熟知的几何图形,但看越久却越发现当中的规则混乱,扭曲的角度完全违反已知的建筑学与物理学,延伸的每个编角几乎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弯曲,而彼此之间根本没有镶嵌的稳定性但却能稳固的相连。
艾瑞克感觉到脑袋痛欲裂,理智在濒临崩溃的边缘,他很不得挖出自己的双眼只求不要再看到这些恶心的建筑,然而他却无控制自己的身体,他忍不住想将眼前的一切尽收眼底,那些怪形的建筑体散发出强大的魅力,让少年径自的往前移动。
紊乱的思绪与开始碎裂的理智,耳边是低沉的细语,艾瑞克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,他沿着建筑体内的阶梯往上移动,他没看到任何生灵,但他确信那些失踪的士兵就在里面,他不知道基地里的那些人怎样了,艾薇娃被吃掉了吗?
老人说这些城市的建造者只喜好吃与繁殖享乐,那大概是真的被吃了吧。
少年的步伐变的沉重,他没有看到任何一丝生气,彷佛这是座鬼城,建筑的壁面乍看带着岩石的纹理,但触感却如同金属般光滑,灰色的壁面没有光泽,一切都是呈现消光色调,艾瑞克将火把凑近端详着壁面的纹路,紧接着,他惊恐地发现那上面刻着的是自己熟悉的文字,少年踉跄向后退却不小心撞进一个窗格子里,他整个人跌进了无人的空间,他慌忙爬起身四处找寻出口,宽广的通道可以看到一点建筑体的内部构造,那似乎是一种诡异的白色发光体,他没看到任何生命体,只是一味地奔跑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他从一个狭小的隧道钻出来,这里又回到了建筑群的走道上,艾瑞克靠在墙边大口喘气,他已经无法理解眼前的现况了,但内心涌现的欲望却促使他继续移动,他想知道这座城市的建造者,他想知道那个曾经屹立在这片土地上的文明。
当他绕到走到尽头的转角时,前方是一个看起来由各种多边形堆积而成的尖塔,尖塔基部则有粗壮的连结构造银深到远方的蜂巢状建筑体,尖塔表面同样刻满了艾瑞克熟悉的文字,那些字体歪斜尖锐令人难以直视,天知道刻字的人当时是什么心理状态,他甚至能感觉到文字主人透过书写发出无声的尖叫。
地面发出细微的震动,少年感觉到空气中有股无形的波动,也许伊娃就在前面?
前面肯定有什么,艾瑞克拖着步伐前行,前方似乎是山里的构造,这座建筑体应该有一部份是镶嵌在山里的,或者是说在经年累月中被群山覆盖,走道两侧直达顶端的山壁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叶扇结构,艾瑞克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用途,但有可能是通风构造,这是他脑中所能联想到最接近的用途,接着,他又看到了浮雕,这些浮雕的表面相当光滑,几乎没有风沙侵蚀的痕迹。
艾瑞克伸手轻抚着浮雕,那些故事彷佛真实呈现在他脑中,透过触摸的指尖传入他脑里,那些奴隶没有固定形体,牠们随着每下移动变化出部一样的外貌,接着艾瑞克看到了,那些奴隶的主人们,厄尔库埃罗彼此摇摆身躯像是某种仪式的舞蹈,圆筒状的身躯庞大又骇人,顶端那个轮廓类似生殖器但却又是极为怪异的模样,腥红的眼珠遍布在类生殖器顶端,这才是这些建筑创造者的模样,酷似昆虫的翅鞘一开一阖发出诡异的节奏,那些诡谲的音色单调又毫无规则可言,而他们伸展的柔软触角彼此交缠收缩。
这是普通的祭祀舞蹈,是每天都会上演的节目,奴隶的主人们在这些飨宴中尽情舞蹈演奏,同时也不停吞噬奴隶带来的美食,除此之外,厄尔库埃罗圆筒状身躯的下半部几乎是一直维持相连的动作,布满皱褶与疙瘩的穴口相融甚至让人难以分辨出是属于谁的,艾瑞克的目光难以从这些可怕的存在身上移开,穴口间缝喷溅出腥臭的黄绿色黏液,这当中甚至还有第三者将这些黏液抹在自己身上,而那些圆筒身躯接近顶端的位置长满大小不一的圆孔,那些圆孔不停开阖将奴隶奉上的食物蚕食殆尽,就如同老人所言,他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一直在保持着繁殖的欢愉。
而那些奴隶,那些阿尔卑斯山的牧羊犬一方面持续供奉着美食,另一方面也尽责的指引访客们加入主人的欢愉,艾瑞克也看到几只牧羊犬的形体交融,牠们不知道是正在模仿主人还是真的体会当中的欢愉,奴隶没有自己的形体,牠们是仿造远古种族的修格斯所创造的,但与之相比却相对有基础轮廓,艾瑞克甚至看到那些不断变化的形体在高潮的抽搐中,显现出一些他熟知的动物肢体,那或许是过去牠们拟态过的动物。
那些交杂的可怕魔音刺激着少年的耳膜,他抽回手靠在墙边瑟瑟发抖,那些影像几乎是深深烙印在他的视网膜里,那些挥之不去的可怕梦魇彷若真实,那些来自过去的故事到现在仍旧持续,艾瑞克知道他们挖得太深了,他们并非唤醒任何东西,而是在对于那些东西发出了询问,而现在就得到了回复。
远方的走廊尽头传来了低鸣声响,艾瑞克皱起双眉缓慢的沿着墙面前进,这里没有出现在刚才的回忆中,这里是建筑体的中心而非刚才幻觉里飨宴的地点,这是什么地方?
少年心里浮现出一丝疑问,他感觉身体每个部位都在发出抗议,酸痛与烧灼感片布全身,他听见了那些可憎的词汇,他也看见了可怕的光景,但他仍旧没有停下脚步,他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,那个深埋在阿尔卑斯山下,这座伟大建筑群的中心。
而就在他拐过弯来到了尽头看到了中心的白色发光体时,他几乎是下意识放声尖叫,他的理智彻底被击垮,他无意识的撒腿狂奔,眼前的景象模糊混乱,那些根本是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恐怖,当狂风呼啸刺痛他的耳膜时,他已经连滚带爬的爬回了洞穴出口,他不敢回头看着那深沉的漆黑洞窟,彷佛一回头就会被无数的触手拖回万丈深渊,他唯一知道的就是逃跑,不管发生什么事,就是彻底逃离这里,远离这个可布之境。
1944??
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多久了,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,我问过无数次这里的护士,她们的说词都一样,我是在援军到达时被发现昏倒在洞窟外,整个基地只剩下我还活着。
我的记忆一片混乱,我记不起来自己那晚所看到的事,他们在基地搜索了一整天,没有任何尸体,那个被封住的储藏尸体洞穴也是空无一物,而我们先前挖掘的隧道被崩塌的落石掩盖住无法通行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
在那个被掩埋的基地哩,肯定有某种东西在那里,就在那片废墟里,在那座山中,我内心有个声音是这样肯定的,但上级似乎也没打算浪费时间在那上面,据说柏林那边已经放弃开掘隧道的事。
我不知道我到底看到了什么,纵使我努力回想也得不到解答,上级很快就放弃对我得询问,同时也告知我过几天就能回家,他们不需要一个疯子士兵,因为我每到深夜都会被自己的凄厉尖叫给惊醒,在梦里,我一次次回到那个深渊地下都市里,但那个光,那个可怖的光就在那里,那不是人类可以直视的伟大存在,不,那根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。
那不是言语或文字就能描述的,我也不知道此刻我究竟在做什么,我每晚总能想到那个声音,就在我耳边低语,我一开始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声音,那听着是一种带有节奏的呢喃。
我渐渐觉得,那是一个优美的邀请诗,是的,或许就是那样,我是这样告诉我的主治医师,但他判断那只是压力创伤症候群的一种征兆,但我现在很清楚,我必须回复那个邀约,我很确定我已经看过几次伊娃在空旷的走廊里游荡,我知道他们是来迎接我的。
我在无数的复原时间里祈求着让我能回去那里,那里才是我该去的归属,是的,肯定不会有人理解的,牠们给了我邀请,那我就一定要给予答复,我们挖得太深了,牠们热情地给予我们邀请,所以我也必须要给予答复。
啊啊,是的,我听到了,牠们来了,牠们来带我了,因为我给予牠们肯定的答复。
看啊看啊,就在外面,我听到了脚步声,啊哈,没错,我不会认错的,牠门来了,就在窗外,就在我的房门口,我无法形容此刻心中的喜悦,来了,牠们已经在催促我要出发了,那些阿尔卑斯山的牧羊犬。
——完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