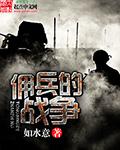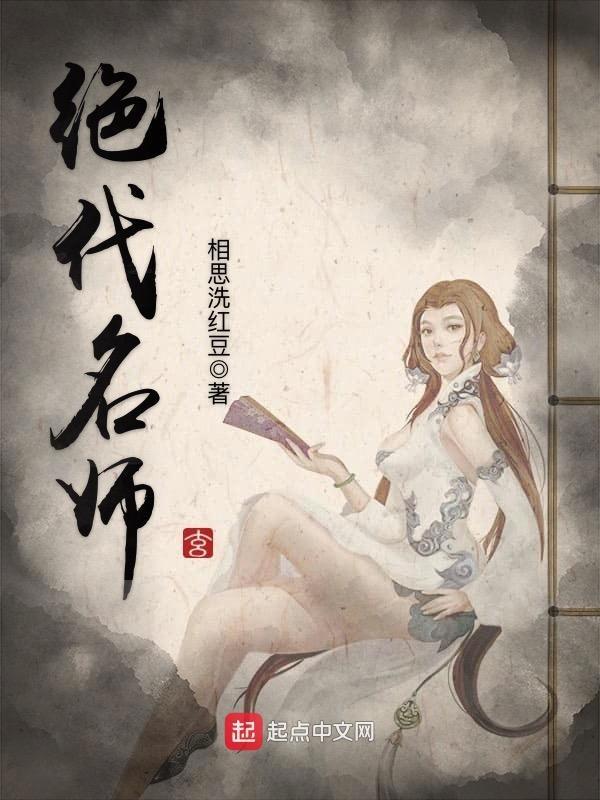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我的哥哥是高欢 > 第238章 你爹不是高渊(第1页)
第238章 你爹不是高渊(第1页)
工部捣鼓的东西还有很多,但目前来看就只有回回炮跟八牛弩取得了不错的进展。
高羽倒也不着急。
这种事情本就急不得,让手底下的人慢慢去琢磨研究便是。
他甚至还特意抽空去看了一眼火药的情况。。。
风雪停歇的第七日,高念的灵柩终于抵达邙山。山路崎岖,送葬队伍缓缓前行,百里素幡在晨光中如云海翻涌。沿途百姓扶老携幼,跪伏道旁,手中桑叶叠成小塔,置于路心,以示敬意。孩童们低声吟唱那首传遍南北的歌谣,声音稚嫩却坚定,仿佛大地深处传来回响。
“黄河清,泰山崩,
高家兄弟定乾坤。
不求封侯拜将台,
但使人间无饥寒。”
书院门前的老槐树下,早已搭起白布灵堂。高念的遗像悬于正中,眉目沉静,嘴角微扬,似仍含着讲学时那一缕温煦笑意。那双并排放置的布履被供于案前??一双破旧,补丁层层叠叠;一双崭新,针脚细密匀称。左脚底绣着“不忘”,右脚底缀着“前行”,墨线清晰,力透布背。
弟子们守灵七日,昼夜不息。有人抄录《铁脊名录》全文,准备刻碑立于边关;有人整理高念三十年来授课笔记,拟编为《民本集》传之后世;更有几位来自幽州、契丹的胡裔学子,自愿北上接替戍边巡查之责,言称:“先生教我们识字明理,今当以身践义。”
第七夜子时,忽有异象。天边无星无月,却见一道淡青色流光自北方疾驰而来,掠过邙岭,直落书院后园。守夜弟子惊起观望,只见沈艺墓旁那块新碑之上,青鸟再度栖落,羽翼沾雪,喙中衔一卷竹简。它轻轻放下,振翅三圈,倏然隐入夜空。
竹简以麻绳捆扎,外覆油皮,完好无损。启封后,内书三行古篆:
>“羽令重归,魂脉未断。
>阴山以北,有城名‘归仁’,藏档千卷,记铁脊三代事。
>持此简者,可启地宫石门。”
众人骇然。这字迹竟与高羽亲笔极为相似,且所言“归仁城”从未见诸史册。次日清晨,消息传至长安,皇帝即召枢密院议事,命薛承志率精骑三千,护送高念门下大弟子李昭远赴阴山寻访。
李昭乃陇右流民之子,十岁入书院,资质平平而意志坚韧,曾徒步千里代师查访屯田弊政,深得高念器重。临行前,他在高念灵前焚香叩首,取走那双新制布履,穿于足上,朗声道:“弟子不敢忘左足之训,亦不负右足之志。”
队伍出雁门关时,春汛初动,冰河裂响如雷。沿途所见,昔日荒芜之地已渐复苏,烽燧林立,炊烟袅袅。每至一处哨所,戍卒皆列队迎拜,称其为“持令使者”。李昭不敢居功,只言:“我非英雄,不过继灯之人。”
二十日后,大军抵至阴山南麓。按竹简所示方位搜寻半月,终在一处断崖之下发现隐蔽洞口,其上石刻“归仁”二字,风化严重,几不可辨。薛承志命工兵清理积土,露出一道厚重石门,门心雕有展翅青鸟图腾,下方嵌一铜槽,正与高念遗物中的“高羽令”形状吻合。
夜半,李昭独自持令上前,双手颤抖将令牌插入槽中。刹那间,地底轰鸣,石门缓缓开启,寒气扑面而出,夹杂着陈年墨香与铁锈之味。门内是一条狭长甬道,两侧壁龛中整齐排列陶罐,罐身标号,依稀可见“柒拾壹”、“柒拾叁”等字样。再往深处,乃是一座巨大石室,中央设青铜案,其上堆满竹简帛书,最上方压着一封黄绢信札,封口未拆,朱砂印文赫然是??“高羽绝笔”。
李昭跪地捧读,泪如雨下。
信中言:归仁城原为东魏末年秘密营建的边防中枢,专司铁脊营调度与档案保存。武定七年,高羽深知门阀势大,新政难久,遂暗设此地,将铁脊营改制为隐形防线,成员永不得归乡,子女不得仕宦,唯以铜牌编号相认。他本人死后,亦令心腹将其棺椁秘葬于此,不立碑,不记名,只求“魂伴孤军,共守北疆”。
又云:“吾一生行事,唯问本心。废九品、清隐户、行均田,皆为抑豪强而养黎庶。然权柄在手,杀伐难免,或有冤者,或有过者,吾不敢辞其咎。唯愿后人不以成败论是非,不因讳忌掩真相。若有一日民心离散,则非敌国之祸,实自我之亡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