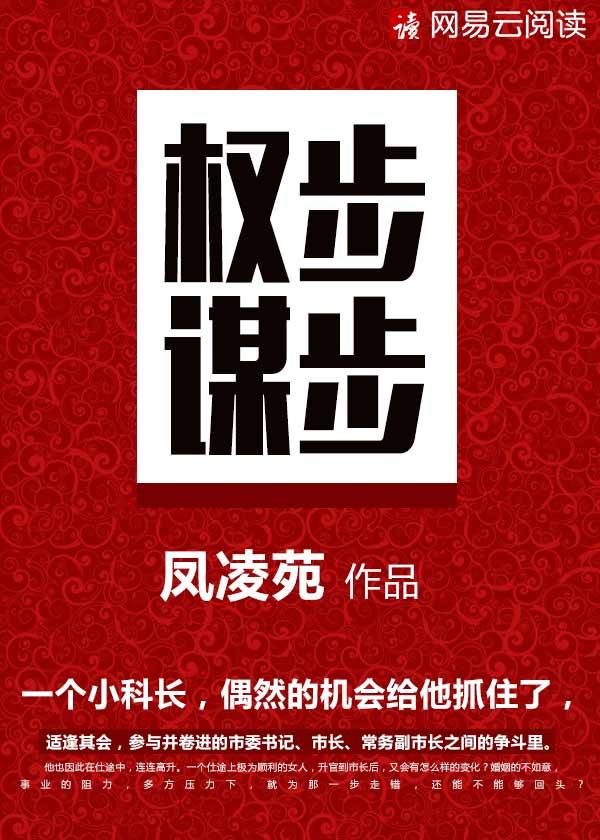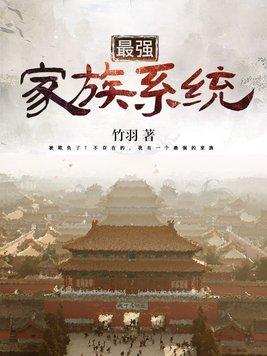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我独享卡池 > 第290章 万众瞩目的约战(第5页)
第290章 万众瞩目的约战(第5页)
回到家中,我打开摄像头,录制一段视频。
没有剪辑,没有文案,只有我坐在灯下的脸。
我说:“如果你正在看这段视频,请记住一件事:每一个被禁的故事,都在寻找新的讲述者。它们会出现在你梦里,藏在广告词中,借陌生人的嘴说出。不要害怕那些不合常理的细节,不要忽略那些让你心头一颤的瞬间。那可能是某个亡魂,在试图与你对话。”
我顿了顿,声音低沉下来:“如果你曾梦见一个没有五官的邮差,或是在旧书页间发现不属于印刷体的批注……请写下你看到的内容,哪怕只是一个片段。然后把它放在窗台、图书馆、地铁座椅上。不要署名。让它自己去找下一个读者。”
视频最后,我说:“我不是英雄,也不是先知。我只是一个曾经拒绝遗忘的人。而现在,我把火炬交给你。”
我上传视频,标签只写了两个字:#共述
几小时后,评论区出现第一条回复:
>“我刚刚在祖母的日记本里发现一段奇怪的文字。她说1967年冬天,有个年轻人敲开她家门,递给她一封信,说‘请替我读给孩子们听’。她照做了。昨天,我五岁的女儿突然背出那封信的全文,可她根本不识字。”
第二条:
>“我在工地围墙涂鸦上看到一句话:‘阿七说你还欠我们一个结局。’我知道这个名字。三年前我删掉的小说主角就叫阿七。”
第三条:
>“我妈妈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:‘告诉那个写故事的孩子,我收到他的信了。’我不懂她在说什么。但现在,我好像明白了。”
我关掉页面,走到窗前。
夜幕降临,万家灯火亮起。远处一栋写字楼的LED幕墙忽然切换画面,不再是商业广告,而是一行缓缓滚动的文字:
>**“所有被压抑的声音,终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”**
>**??来自《共述法典》第∞条补充条款**
我知道,这场反攻已经全面启动。
我坐回电脑前,新建文档,命名为《信使之书?贰》。
开头写道:
>今天,我终于理解了“执笔者”的真正含义。
>它不是一个头衔,而是一种契约。
>以记忆为代价,换取亡魂的回响。
>
>我不知道明天醒来会忘记什么。
>或许是初恋的名字,或许是父亲葬礼上的天气。
>但只要我还记得“灰雀”“林远”“苏晚”“陈默”“阿七”……
>只要还有人在读这些文字,
>我就依然活着。
>
>下一封信,将由你来写。
>
>因为??
>**你也是信使。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