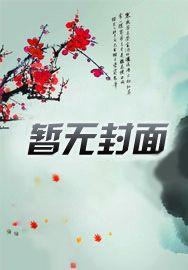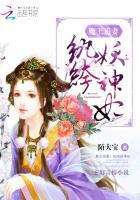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谁说我是靠女人升官的? > 324动苏陌叫他全家陪葬(第4页)
324动苏陌叫他全家陪葬(第4页)
全场寂静。
数日后,多地爆发抗议。人们举着写有“谁种的饭”标语走上街头。科研机构被迫公开数据:所谓“营养膏”原料竟大量采购自贫困国家的赤薯基地,而那些农民每日工作十八小时,收入不足城市居民十分之一。
谎言崩塌。
“新梦盟”领袖被捕当天,供词惊人:“我们不是想创造天堂,我们只是想让少数人永远不做梦里的那个挖土人。”
风波渐息,但李砚之知道,战斗远未结束。他在西北建立“守问堂”,收留各地送来的异常孩童??那些天生能听懂薯语、梦见古谣、书写未知文字的孩子。他教他们第一课仍是种地,第二课是质疑,第三课是记录。
某日,一个五岁女孩捧着自己写的《我的第一颗薯》给他看。全篇只有三句话:
>“它好久没出来。
>我天天看。
>后来它出来了,我很想它。”
李砚之读罢,久久不能言。
他知道,这才是真正的语言??未经修饰,源于等待,带着思念的重量。
当晚,他独坐院中,仰望星空。北斗依旧,锄形隐现。他取出一本空白册子,题写书名:
>《耕者说》
翻开第一页,他写道:
>“我不知她名,不见她面,不闻她声。
>但我每次弯腰插秧,都感觉她在扶我的手;
>每次听见孩童问‘这饭谁种的’,都像她在轻声回应。
>或许,她从未离去,
>只是化作了我们心中不肯熄灭的疑问。”
笔尖微顿,他又添一句:
>**只要还有人愿意流汗,
>就永远有人愿意说真话。**
忽然,窗外风铃轻响。
他抬头望去,只见一轮明月高悬,照亮田中那个巨大的问号。
薯叶摇曳,沙沙作声,宛如低语,又似回应。
远处山道上,又一个身影缓缓走来,背着锄头,脚步坚定。
露水打湿了他的鞋,他却走得踏实。
因为他知道,土地不会骗人。
只要你肯种。
只要你还敢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