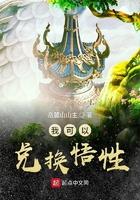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为变法,我视死如归 > 第245章 章惇有罪个人战和团体战不是一个打法的(第2页)
第245章 章惇有罪个人战和团体战不是一个打法的(第2页)
数十里外,登州海岸,百门“鸣雷弹”齐射升空。炮弹未带火药,只填满碎瓷与铁钉,却在空中引爆,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。声音借春风远播,如雷霆滚滚压境。辽军战马受惊,纷纷人立嘶鸣,阵型大乱。
萧禧面色惨白,望着南方苍茫大地,喃喃道:“这不是火器……这是天威。”
四月十五,辽使团仓皇北返。途中,一名随从不慎落马,摔开行囊,竟滚出数十枚宋制铜钱。当地百姓拾起一看,皆是“熙宁通宝”,背面却刻着极小的汉字:“火眼之下,莫藏奸谋。”
消息传回汴京,赵顼大喜,欲加王小仙爵位。王小仙坚辞不受,反奏请减免河北三路赋税两年,并将火器监部分收益拨作“工匠抚恤金”,凡研制中伤残者,终身俸禄由国库承担。
朝中旧党讥讽:“此乃收买人心。”
王小仙只淡然回应:“人心不是收买的,是用命换来的。”
五月,兰州研究院全面复工。阿骨打在离日前,亲手绘制《女真地形火器布防图》,悄然留于工坊案底。张九章发现后,未上报,而是将其焚于炉中,只将关键数据默记于心。
六月,第一批党项学徒完成学业。王小仙亲自主持结业礼,每人赐《惠民册》一本、铁锄一柄、良种十斤,并宣布:“三年之内,凡在西北兴办工坊者,免税五年;所产器械,优先售予官府。”
一名少年哽咽叩首:“我父兄死于宋夏之战,今日方知,原来汉人也能给我们活路。”
王小仙扶他起身,朗声道:“从前是仇,今后是家。刀剑能断骨肉,却斩不断黄河之水。你们学会的不只是铸炮,更是如何不让炮口对着自己的同胞。”
秋七月,京东路蝗灾。朝廷开仓赈济,却仍有流民聚众抢粮。地方官请调军镇压,王小仙否决,反命人将库存“药露汤”加倍稀释,沿路设棚免费施饮,并招募流民修筑堤坝,以工代赈。
有幕僚忧心:“此法耗财甚巨,恐损国库。”
王小仙立于河堤之上,望着万千百姓挥汗如雨,轻声道:“国库空了可以再满,民心散了,百年难聚。”
冬十月,辽国传来惊人消息:南院大王耶律仁先病逝,临终前留下遗言:“宋不可伐。王小仙在,如日悬空,影不西斜。”
赵顼闻之,在紫宸殿设香祭拜,感慨道:“朕得此臣,胜得十万雄兵。”
王小仙却在当夜独自登上宣德楼。北风凛冽,吹动他半白的鬓发。他望着辽东方向,低声自语:“耶律仁先,你错了。我不是太阳,我只是点燃火把的人。真正的光,还在远方。”
十一月二十,兰州再次传来捷报:第四尊震天炮试射圆满成功,精准命中三十里外靶标,误差不足三步。更令人振奋的是,党项学徒主导的“轻装火箭车”研制成功,可由四人推动,连发九箭,适合山地作战。
王小仙看完奏报,久久不语。他提笔写下一道密令:“准许兰州研究院对外展示‘火箭车’模型,邀请辽、高丽、西夏使节观礼。”
宋玉大惊:“相公是要示弱于敌?”
“非示弱,是示道。”王小仙微笑,“让他们亲眼看看,我们的技艺不止于杀人,更可用于修桥铺路、开山引水。若有一日,他们不再想打仗,而是来求一门手艺、一包种子,那才是变法的真正胜利。”
腊月初八,佛成道日。汴京大雪纷飞。王小仙于府中煮粥施僧,忽闻门外喧闹。开门一看,竟是数百名工匠携家带口冒雪而来,为首者正是张九章。
“相公!”张九章跪地捧上一只木匣,“这是兰州全体匠人所铸‘太平铃’,以废炮铜熔炼而成,内刻三百二十七名殉职工匠姓名。我们请求,将此铃悬挂于火器研究院门前,每日晨昏一响,既悼亡魂,亦警后人。”
王小仙双手颤抖,接过木匣。铃身粗糙,却沉甸甸的,仿佛压着无数未眠的魂魄。他缓缓点头:“挂吧。但铃上加一句??‘变法不死,薪火相传’。”
那一夜,他再度提笔,在《火器图谱》末页补写道:“世人谓我好权、嗜杀、悖祖、逆天。然我所求,不过让牧童能读书,农妇免饥寒,边卒不必白骨埋沙。若有来世,仍愿为薪,燃尽此身。”
次日清晨,雪霁天晴。第一缕阳光照在宣德楼顶,映得琉璃瓦如金波荡漾。宫门开启,百官入朝。忽闻西城方向钟声悠扬,绵延不绝。
那是兰州传来的消息??太平铃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