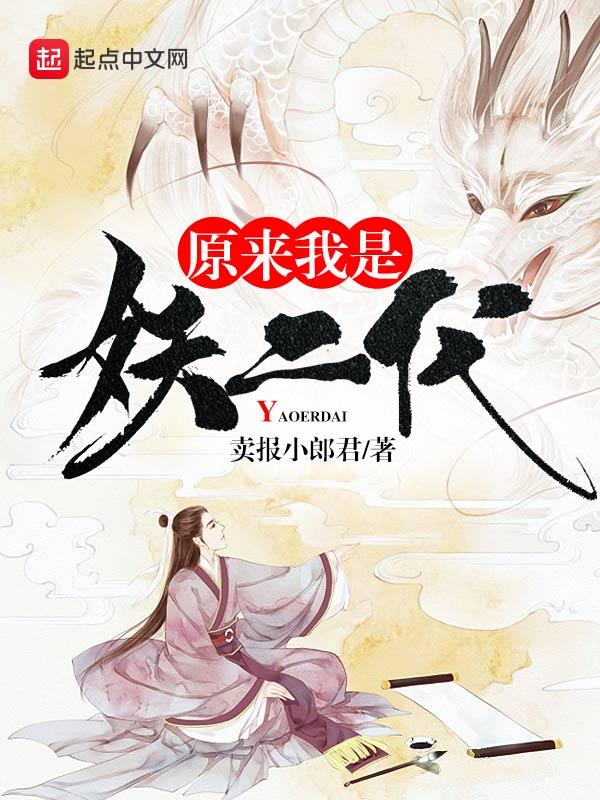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华娱的盛宴 > 第221章 勇敢(第1页)
第221章 勇敢(第1页)
在首都歇了两天。
但其实也基本上没怎么见外人,甚至他此番来了又走,短短两日,都基本上没几个人知道他回来过??陈虹、许卿、蒋琴琴、左小倩,居然那么巧的,全都在外地拍戏中。陈虹在拍《燕子李三》,许卿。。。
九月的北京,早晚已有凉意。林见鹿清晨五点便醒了,窗外天色灰蓝,楼下的银杏叶开始泛黄,风一吹,打着旋儿贴地滑行。他披衣起身,泡了一杯浓茶,坐在书桌前翻看“无围墙音乐学院”结业生提交的“百人共唱”活动总结报告。每一页都附着照片、录音链接和村民手写的感谢信,字迹歪斜却真挚。
他点开一段视频??甘肃陇南的一处山村小学操场上,六十多个孩子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,围成圆圈跳着羊皮鼓舞。领舞的是个八岁的小女孩,左腿微跛,但动作坚定有力。她父亲在三年前修路时被落石砸中瘫痪,母亲离家出走,是村里老艺人收留了她,教她打鼓、唱古谣。如今,这孩子成了全村最会敲鼓的人。
林见鹿盯着屏幕,眼眶微热。他记得这个村子,去年冬天他曾随团队去采风,那天下着雪,教室漏风,孩子们的手冻得通红,却坚持把一首《祈年调》唱完。当时他就说:“这里的孩子不该只背乘法口诀,他们更该记住祖先怎么向天地开口。”
手机震动,刘晓丽发来消息:**“教育部刚批复第二批‘活态传习中心’试点名单,新增十八个县,涵盖东北赫哲族聚居区、青海土族村落、海南黎寨……你下周得去趟长春,那边的老渔民要给你唱《乌苏里船歌》原生态版本。”**
他回了个“好”,又补了一句:**“告诉他们,别准备舞台,就在江边船上唱。”**
清晨七点,他出门散步,顺路去了胡同口那家开了三十年的烧饼铺。老板老张见是他,咧嘴一笑:“林老师,今儿加个蛋?”不等回答,already把鸡蛋打了进去。街坊都知道这位“大人物”从不讲究排场,常穿旧布鞋、拎帆布包,买完烧饼还顺手帮邻居抬煤气罐。
“您说这民歌真能救人心?”老张一边刷油一边问,“我孙子天天刷抖音听那些山沟沟里的调子,居然不打游戏了,还非闹着暑假去贵州住寨子。”
林见鹿咬了一口滚烫的烧饼,芝麻簌簌掉落。“不是民歌救人,是它让人听见自己。”他说,“城里孩子听腻了编曲完美的流行歌,突然听到一个老太太在灶台边哼童谣,那种粗糙的真实,反而戳中了心里最软的地方。”
正说着,旁边一个骑电动车的年轻人停下车,摘下头盔喊道:“林老师!我是延川县的,我们村现在每周六晚上搞‘火塘音乐会’,您啥时候来看看?”
林见鹿笑着点头:“记下了,排进日程。”
回到家中,他打开电脑,开始起草一封公开信,标题拟为《给所有愿意发声的人》。写到一半时,温眉钧来电,声音带着高原特有的清冽:“老师,我在甘南迭部,刚完成一轮‘声音地图’测绘。我们在一座废弃经堂里发现了十二卷手抄诵经谱,纸页脆得像枯叶,但AI扫描还原出了七段失传的‘嘛呢吟诵’。”
“干得好。”林见鹿轻声说,“尽快做数字化归档,然后交由当地寺院自主管理。技术是桥,不能越俎代庖。”
“明白。”她顿了顿,“我还带了几个藏族学生用手机录‘雨后林间声景’??鸟叫、溪流、松针滴水,混进一首即兴创作的‘自然复调’。昨晚上传播客频道,两小时破十万播放。”
“这才是真正的现代传承。”林见鹿笑了,“你们不是在复制过去,而是在让传统呼吸今天的空气。”
挂了电话,他继续写信:
>……有人问我,“山河计划”到底想做成什么样子?
>我想,它不该是一座纪念碑,而应是一条河。
>河水来自雪山融雪、林间细流、村妇洗衣的拍打、牧童放牛的口哨。它不拒绝支流,也不规定流向。
>只要还有人在土地上生活,在苦难中歌唱,在喜悦里起舞,这条河就不会断流。
>所以,请不要叫我“发起人”。我只是第一个蹲下来听河水说话的人。
信末,他附上一组数据:全国已有三百七十六个村庄自发组织“日常传唱日”;一百四十二所中小学将地方民歌纳入课间广播;三十七所高校开设“田野音乐学”选修课;抖音#我家的歌话题累计播放量突破四十亿次。
当天下午,他受邀参加一场特殊发布会??由中国移动联合“山河计划”推出的“乡村声音基站”正式上线。这不是普通的通信工程,而是一项文化基础设施:在偏远地区建设具备录音、存储、传输功能的微型基站,村民可用方言录制歌曲或故事,自动上传至“大地耳穴”云平台,并生成专属二维码。亲人扫一下,就能听到家乡的声音。
发布会上,一位云南怒江的傈僳族老人现场演示。他对着话筒唱了一首《迁徙之歌》,歌声苍凉悠远,讲述祖先翻越高黎贡山的艰辛。三分钟后,系统生成二维码,他颤巍巍掏出老年机,扫码播放,听着自己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,忽然老泪纵横。
“这是我第一次,听见自己唱歌。”他说。
台下寂静片刻,随即掌声雷动。
林见鹿站在侧幕,默默注视这一幕。他知道,这一刻的意义远超技术本身。多少世代以来,这些声音从未被记录,未曾被尊重,甚至被视为“落后”的象征。而现在,它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数字身份。
散场后,他独自走在长安街上,暮色四合,华灯初上。手机再次响起,是阿依库的消息,附带一段音频文件:**“老师,这是我们乐团的新编曲,《喀什噶尔谣》交响版,用了冬不拉、艾捷克、手鼓,还有我自制的沙瓶打击乐。您听听,像不像戈壁上的风?”**
他戴上耳机,按下播放。
前奏是低沉的大提琴模拟沙暴呼啸,紧接着冬不拉切入主旋律,清亮如月光洒落荒原。中段加入多声部轮唱,少年们的嗓音交错起伏,宛如群鸟掠过天际。最后,一段沙瓶节奏渐强,汇入全乐队齐奏,磅礴如日出熔金。
曲终,他久久未语。
那一刻他忽然明白,所谓“振兴”,不是把老东西供起来,而是让它长出新的翅膀。
一周后,他飞抵长春。松花江畔,几位年过七旬的老渔民早已等在岸边小船上。他们没化妆,没换演出服,只是穿着褪色的棉袄,戴着毛线帽,手里握着桨和渔号角。
“林教授,咱不唱给你们听,咱唱给江听。”为首的老人说。
船离岸,驶入江心。秋雾弥漫,水面如镜。忽然,一声高亢的号子划破晨霭:
>“哎??嘿哟!乌苏里江长又长哟??
>鱼儿肥来网儿张哟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