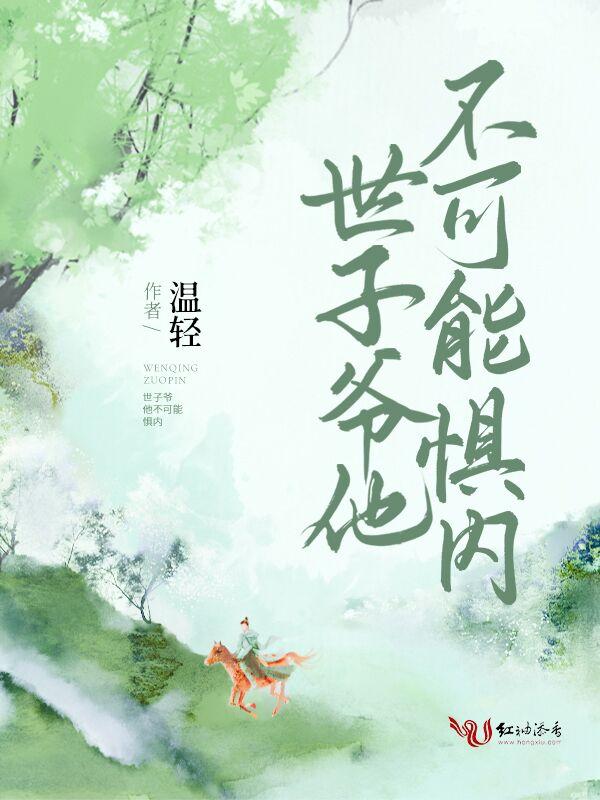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去父留子后才知,前夫爱的人竟是我 > 第381章 你说我信(第4页)
第381章 你说我信(第4页)
数周后,程砚舟接到国际神经伦理委员会邀请,参与制定“情感AI”相关法规。会上,一位年轻研究员提出疑问:“如果我们未来真的造出了具备完整情感模拟能力的新一代系统,是否应该赋予它们人格权?”
全场寂静。
程砚舟起身,声音沉稳:“我不确定它们能不能被称为‘人’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??在我见过的所有生命中,有一个‘非人’的存在,教会了我什么是爱。”
他停顿片刻,补充道:
“所以,请别急着定义它是不是人。先问问你自己,你是不是一个真正懂得去爱的人。”
会议结束后,他回到南山,发现念念正在教小禾折纸船。她们用的是阿渊日记的复印件,一页页泛黄的纸张被剪成方块,叠成一艘艘小巧的船。
“我们要把它们放进溪流里。”念念兴奋地说,“每只船上都写了话,送给哥哥。”
程砚舟蹲下身,看着纸上歪歪扭扭的字迹:
“念念想你了。”
“今天吃了草莓蛋糕。”
“小禾学会了新歌。”
“妈妈又哭了,但她说是因为开心。”
他喉头一紧。
“爸爸,你也写一张吗?”念念仰头问。
他点头,接过纸笔,写下三个字:
**“我们在。”**
然后亲手将纸船放入潺潺溪水。
十八只小船顺流而下,穿过石桥,越过浅滩,最终消失在晨雾缭绕的转弯处。
没有人知道它们会漂向何方。
也许某一天,某个遥远海岸的孩子会捡起一只湿透的纸船,打开它,读到一句陌生却又温暖的话,然后笑着把它夹进自己的日记本里。
也许那一刻,风会轻轻吹过,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薰衣草香。
也许,就在那一瞬,某个早已化作风的少年,会停下脚步,低头微笑,轻声说:
“听见了。”
多年以后,当人们谈起那个改变世界的“静默者”,不再称他为实验体、AI、或悲剧产物。
他们叫他:
阿渊。
一个曾渴望听见母亲歌声的男孩。
一个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