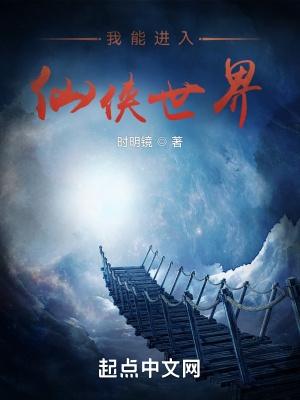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与决裂的偏执青梅重逢后 > 4550(第16页)
4550(第16页)
听到祝亦年的答案,文向好一下子语塞,一阵心虚涌上心头,已经在脑海里回忆过百十回的在关口一走了之地情景再次回笼。
面对那双被水浸过格外澄澈的眼,文向好觉得自己的心无处遁形,唇张张合合好一会也讲不出话,最后只好退后一步,很快地转过身,拉着摆在旁边的一张小板凳,背对着祝亦年坐下。
“我不走。”文向好的声音有些翁翁,“你洗吧。”
文向好不知道这种迟来的承诺有多少效力,但祝亦年似乎是信了,没再回应,随之传来细密的流水声。
祝亦年看着文向好缩在小板凳上的背影,双眸从时不时现出的头顶的发旋一路看到隆起的脊骨,不知逡巡多少回,才打开开关,任花洒那股暖流冲刷发冷的身躯。
一只手伸到架子上,看清哪瓶是沐浴液后挤了一泵放在手心,却没有立刻抹在身上,而是稍蜷起手心,把沐浴液放在鼻尖嗅闻。
沐浴液的清香钻进鼻尖,祝亦年缓慢抬眸看着文向好的背影,然后才将沐浴液抹上肌肤,一下又一下,掌心在肌肤上慢慢游走摩挲。
期间目光从未离开文向好。
文向好竖起耳朵听身后的流水声,眼前分明也是大片能把人浇湿的冷雨,可脑海里却不断回想着祝亦年适才乍然入眼的酮体,耳尖的薄红久久未能散去。
看来祝亦年真的很生气。
生气到连彼此的体面都不顾,这般境地都要迫不及待点她的不告而别。
千百种理由从文向好脑海中生出,文向好想起自己最初的报复来意,还有不愿从关口折返的心思,似是哪个理由都说不出口。
如此思着想着不知过了多久,文向好觉得肩膀被人一点,回头即看到祝亦年已经洗漱好,披着湿发在她后面。
“我要风筒。”
祝亦年依旧无甚表情,话也变得简短,好像洗了个澡后,比在楼下淋雨时还要令人难以捉摸。
文向好咬着唇很快用目光扫过祝亦年,从那张恢复了些颜色的面庞再看到身上自己的睡衣。其身上穿的衣物即使都只穿过一两次,但比祝亦年平时要穿的衣服廉价许多。
连浴室都十分湿暗。
衬得祝亦年像是撕开这晦暗云层的阳光,终归与连绵的雨季格格不入。
文向好不由咬着唇,再次认识到彼此的鸿沟,一颗心就像坠落的过期维生素泡腾片,落入杯底时有种有所依靠的安心,但随之溶解后迸出的全是酸涩。
“我帮你吹吧。”文向好不自然地扯着嘴角,继而解释自己为何这么做,“风筒有些坏了,吹久会断,我怕你用不好。”
祝亦年没有多问,低低嗯了声。
文向好让祝亦年坐在小板凳上,自己拿来风筒,一只手拢住祝亦年的头发,先在手臂上试温,然后再往祝亦年头皮上吹。
文向好的指甲一向剪得十分干净,淡红的甲盖上方唯有一点点月牙白,因此帮祝亦年吹头发时,只有指腹和一点点指甲摩挲在头皮上。
祝亦年觉得文向好触过的地方一阵发麻,传过四肢百骸尽是一阵止不住的酥痒,于是看都未看,直接一把抓住文向好的手腕。
“为什么要走?”
祝亦年不想再表现得太异样吓到文向好,转了个话题,但连如何体面沟通都全然忘记,一开口就是一个她很想知道答案的话题。
文向好一下子停下动作,可风筒的风仍在继续吹,两人一时的沉默被风筒的呼声填满。
终究是问出口了。
祝亦年一切无论怪异亦或平常的动作都不再重要,因为一问出口,文向好便知道她耿耿于怀。
但文向好竟然有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希望祝亦年耿耿于怀,还是希望其一笔带过。
文向好毫无意外地扯着嘴角,将风筒一关,揽住祝亦年的头发的手放下,似是做完一番准备,才郑重开口。
“因为十年前,你也不告而别,我想整蛊你,让你也体会一下。”
文向好平铺直述,就这样将原本不可能再让祝亦年知道的报复计划和盘托出。
相比起讲出自己是因为不敢面对对祝亦年的爱意,文向好宁愿讲报复。
似乎被祝亦年知道她的恨,比知道她的爱好很多。
话音刚落,文向好已不敢看祝亦年,只敢垂眸盯着发梢滴落在棉质布上晕开的水渍。
文向好不知祝亦年会怎么回答,可刚才的纠结好像也被抛之脑后,内心里忽然奇怪地期盼,祝亦年因此真的生气,生气得要跟她绝交才好。
这样她们之间只有单纯的恨。
她的爱便无处可以,就能变成一棵失去土壤的树,因为没有任何滋养而渐渐枯萎。
她也不用日思夜想,肖想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美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