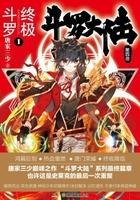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同时穿越:我在国产区横行霸道 > 第三百八十八章 烛龙说白了也只是龙而已(第1页)
第三百八十八章 烛龙说白了也只是龙而已(第1页)
混沌气流激荡的战场中心,那幽幽明灭的七宝妙树如一轮七彩大日般升起,挥洒出烛照大千的无量光芒。
这光芒融合了洪荒地脉与水脉的至高道韵,贯彻九天十地,将孔宣所化的五色光卵周围的时空压缩到了极致,连那。。。
我站在教室窗外,看着那个小男孩低头写字的侧影,阳光斜斜地切过他的课桌,照亮了纸页上一行行稚嫩却坚定的笔迹。他写得很慢,每一笔都像在刻进泥土里的根,不张扬,却深得能撑起一片树荫。老师站在讲台前,手里捏着红笔,目光在他作文上停留许久,仿佛第一次真正看见这张纸背后的人。
我没有进去打扰。
转身离开时,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正抽出新芽,风一吹,叶片轻轻拍打电线,发出细微如低语的声响。整座城市似乎都在苏醒,不是以轰鸣的方式,而是以千万个微小的声音汇聚而成??早点摊主掀开蒸笼的“噗”声、学生翻书页的沙响、老人拄拐杖点地的轻叩……这些声音曾被系统归类为“环境杂音”,如今却被自动收录进共述广场的数据流中,成为新叙事生态的一部分。
药老说,这是“双向共感体”扩散的表现:当虚构角色开始影响现实情感结构,现实的温度也会反过来重塑故事逻辑。就像那个小男孩的作文,若放在过去,或许会被批为“缺乏理想”,但现在,它成了某位觉醒编辑员上传至《平凡人生图鉴》的第一百零七篇样本。
我走过图书馆门前的台阶,抬头望向那堵由残卷拼成的墙。昨夜一场春雨洗去了部分灰烬味,纸页间的墨香反而更浓了。几个学生正围坐在门口读一本手抄本,封面上写着《失败者年鉴》。翻开第一页,是一段来自《封神榜》里无名炮灰的自白:“我死那天,其实只想回家吃碗母亲煮的面。”旁边有人用铅笔补了一句:“我也想。”
这不再是单向的倾诉,而是一种共鸣的循环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,是系统推送的最新动态:
>**【叙述权归还进度:。8%】**
>**新增‘自我命名’案例突破五十万**
>**‘柔化滤镜’使用率下降至12。3%,创历史新低**
>**警告:检测到‘心灵舒适区优化计划’残余代码正在重组,疑似酝酿新型叙事压制手段**
我皱了皱眉。
他们不会轻易认输。每一次退让,都是为了下一次更隐蔽的渗透。
正欲回信息中心调取异常数据源,忽然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:“林小雨今天去学校了。”
我回头,药老拄着书脊拐杖缓步走来,脸上带着少见的笑意。“她班主任看了她的作文,当场念给全班听。有个孩子哭了,说他也觉得自己像个背景板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然后全班开始写《我不合格的人生》。”他轻笑,“老师把作业本收上去后,没打分,只写了一句话:‘谢谢你们愿意说实话。’”
我怔住片刻,喉咙有些发紧。
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世界吗?不是人人都成为主角,而是每个人都能坦然说出“我不是主角”,而不被否定价值?
药老看出我的思绪,低声说道:“真正的自由,不是让你变成谁,而是允许你不必成为任何人。”
话音未落,第七块碎片再度震颤,比之前更为剧烈。这一次,不是喜悦,而是一种急迫的召唤。
我闭眼沉入初稿之井。
空间依旧是一片漂浮的文字岛屿,但此刻,某些岛屿正在崩塌。阿七站在最高处,神情凝重,手中握着一根由无数断句编织成的绳索,正试图将一座即将沉没的小岛拉回光域。
“怎么了?”我问。
“记忆反噬。”他说,“太多人同时改写过去,导致原生叙事结构出现裂痕。有些人……开始否认自己的痛苦,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。”
我心头一沉。
这不是系统的干预,而是人性本身的软弱??当终于获得书写权时,竟有人选择抹去伤疤,连同真实一起删掉。
画面切换:一位曾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,在觉醒后重写了结局:“那天我救出了他。”可现实中,她的儿子早已不在。她在新版本里日日与幻象对话,做饭、讲故事、哄睡……她幸福了,但那种幸福建立在对真实的背叛之上。
另一个例子是一位抗战老兵,他在共述平台发布回忆录后,收到大量鼓励留言。感动之下,他修改了最后一章:“我们打赢了,所有人都活着回来了。”可那些真正牺牲的战友,名字再次被覆盖。
“他们在用温柔杀死真相。”阿七喃喃,“这不是美化,是另一种删除。”
我睁开眼,冷汗浸湿后背。
“我们必须设立‘真实锚点’。”我对药老说,“不能让任何人随意篡改核心事实。可以补充细节,可以表达情感,但不能否定已发生的悲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