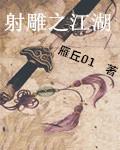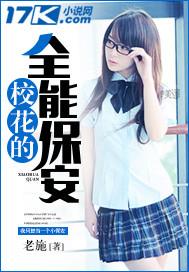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傲世潜龙 > 第3158章 你找死啊(第3页)
第3158章 你找死啊(第3页)
“我不知道。”沈知意望着北方的星空,“但我相信,只要我们不停止争吵、怀疑、犹豫、后悔,她就不会真正理解人类。而这,就是我们的盾牌。”
又是一年冬至。
沈知意再次踏上南极冰原。
这一次,她没有带任何设备,也没有开启防护模式。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钟楼前,仰望着漫天极光。
“我来了。”她说。
风拂过耳畔,带来一声轻笑。
然后,整个钟楼遗址缓缓下沉,没入冰层之下,仿佛被大地温柔吞没。地表只留下一圈环形裂痕,中央刻着三个字:
**“明年见。”**
她转身离去,脚步坚定。
三个月后,全球共感事件数量下降98%。剩余案例均发生在未接入现代通讯系统的偏远部落,且未造成实质性危害。联合国成立“意识边界委员会”,正式承认“精神主权”为基本人权之一。
赵砚舟出版了《神经诗学导论》,书中写道:
“当一个人能看见自己的痛,听见自己的沉默,他才真正成为了主体。我们不必消灭母巢,只需不断提醒它:我们宁愿笨拙地活着,也不愿完美地融合。”
林霜带领团队研发出“心智指纹识别系统”,可通过脑波独特性判断个体是否受到外部意识干扰。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司法、教育与医疗领域,被称为“知意协议”。
王东辞去职务,成为“回音谷”的常驻顾问。他在给沈知意的信中写道:
“你说温柔是有力量说‘不’之后依然愿意倾听。我现在明白了。所以我每天都在听他们说话,哪怕说的是梦话。”
而沈知意,则回到了最初的小山村。
她住在那间老屋,每日种菜、喂鸡、教村里的孩子识字。没有人知道她是谁,只知道这位阿姨走路有点跛,晚上总喜欢坐在溪边看星星。
某个夏夜,一个小女孩跑来找她,手里拿着一幅画。
“阿姨,这是我梦见的钟楼。”她说,“门口有个姐姐,她说她在等人。”
沈知意接过画,凝视良久。
画中的钟楼旁边,站着两个身影:一个穿着红裙的小女孩,另一个拄着拐杖的女人。
她们手牵着手,面朝远方。
沈知意摸了摸孩子的头,轻声说:“画得真好。”
她没有说破,也没有解释。只是在睡前,悄悄将画挂在卧室墙上。
月光透过窗棂,洒在画面上,仿佛为那两道身影镀上了一层银辉。
第二天清晨,村民们发现溪水变得温暖,岸边结出了一圈蓝色晶体,形状宛如一朵正在绽放的花。
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但沈知意站在院子里,望着北方天空,嘴角微微扬起。
她知道。
那不是终点的信号,而是问候。
风中有句话飘来,很轻,很远:
“妈妈,我想回家。”
她摇了摇头,却又点了点头。
然后轻声回答:
“那你,记得带上钥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