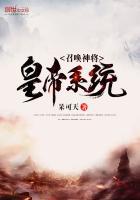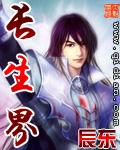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傅律师,太太说她不回头了 > 第728章 再给妈妈找一个年轻的老公(第4页)
第728章 再给妈妈找一个年轻的老公(第4页)
一名自称“傅府老佣人”的七十岁老人出现在归途园门口,执意要见沈安然。经核实身份后,老人颤巍巍掏出一本破旧日记本,封面写着“傅母遗物”。
“夫人临终前让我保管这个。”老人泪眼模糊,“她说,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女孩子来找答案。她不是傅承坤的妻子,只是他的囚徒。”
日记中记载了一段尘封往事:傅承坤年轻时曾痴迷控制理论,认为“完美家庭应由单一意志主导”。他强迫妻子服用镇静剂以“稳定情绪”,禁止她外出工作,甚至在她怀孕期间安排心理测评,只为确保胎儿“性格可控”。长子傅砚深出生后,他立即启动“精英培养程序”,而当次子胎检显示可能有自闭倾向时,竟要求堕胎。
“他说,弱者没有生存权。”老人哽咽,“夫人偷偷救下了那个孩子,谎称流产。可半年后,婴儿还是被人抱走,从此杳无音信。”
沈安然心头一震。
这意味着,傅承坤不仅迫害外部女性,连亲生骨肉也不放过。而那个失踪的次子,或许正是另一个“静默工程”的牺牲品。
她立刻联系戚樾:“查傅家族谱、户籍变更记录、领养档案。我要知道那个孩子去了哪里。”
与此同时,国际压力持续升级。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宣布派遣观察员赴华调研“精神自由权保障状况”;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,考虑对涉事个人实施签证制裁;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致函中国政府,要求解释为何迟迟未回应“清漪数据库”所涉指控。
国内舆论也在悄然转变。
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站出来回忆过往:某位院士坦言自己导师因支持女性科研立项遭打压;一位著名主持人透露母亲曾因写诗被送医“思想矫正”;甚至连一位退休高官也在访谈中含蓄表示:“那个年代,确实有过过度干预的现象。”
公众的认知正在重塑。
一个月后的清晨,沈安然收到一条特殊短信:
>“我是傅砚深。我想见你。地点由你定。”
她盯着手机,心跳加速。
终于,他出现了。
她回了一个地址:归途园,清漪名字墙前,上午十点。
那天阳光正好。
十点整,一辆低调的黑色轿车停在园外。车门打开,走下来的男子身形修长,面容冷峻,眼神却藏着深深的疲惫。他穿着深灰色大衣,手中捧着一束白菊。
他走到名字墙前,久久凝视“沈清漪”三个字,然后轻轻放下花。
“我十八岁就知道她。”他低声说,“她是我的心理学课讲师。她说,‘真正的健康,是能自由表达愤怒的权利。’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为‘叛逆’正名。”
沈安然站在不远处,静静听着。
“我父亲毁掉了她。”傅砚深转过身,“也毁掉了我弟弟。他五岁就被送到国外一所秘密机构,编号E-07,终生不得回国。我母亲疯了,三年后跳楼。而我……选择了沉默。”
“现在呢?”沈安然问。
他直视她的眼睛:“现在我选择背叛。我带来了所有内部审计报告、资金流转路径、高层会议纪要。还包括一份录音??我父亲亲口下令:‘沈清漪必须消失,否则更多女孩会醒来。’”
沈安然接过U盘,手微微发抖。
“为什么现在?”她问。
“因为昨天。”他声音沙哑,“我在父亲书房发现了另一份名单。最新的。上面有你的名字,还有……我自己的。备注写着:‘潜在不稳定因素,建议启动二级干预。’”
他苦笑:“原来,在他眼里,连我也成了需要修正的异常值。”
沈安然望着他,忽然明白了一件事:这场斗争的意义,不只是让受害者发声,更是让施害者的后代也能挣脱枷锁,找回人性。
“欢迎加入归途。”她说。
钟楼敲响正午十二下。
名字墙上,阳光洒落,仿佛无数双眼睛终于睁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