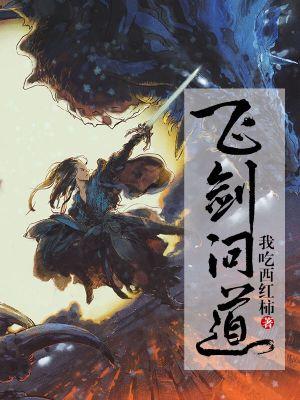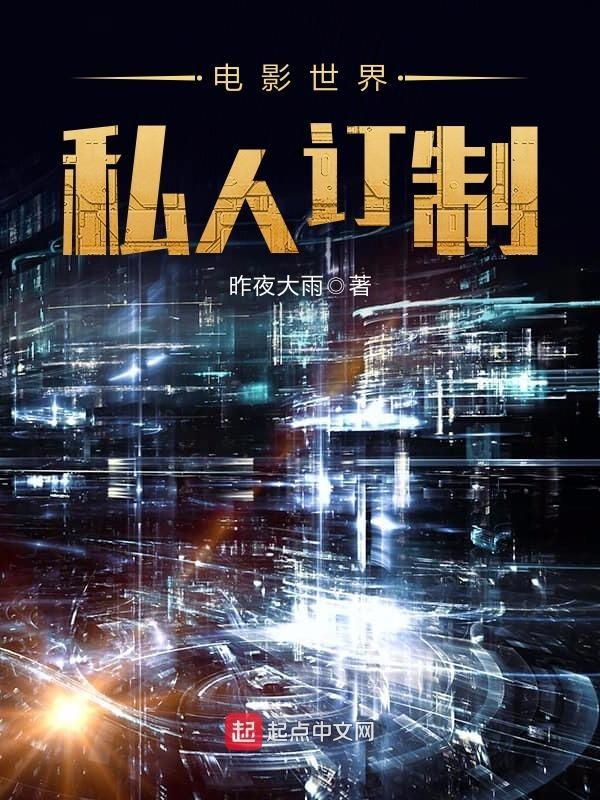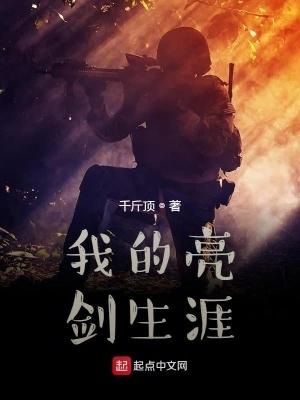我的书库>七零易孕娇娇女,馋哭绝嗣京少 > 第589章找人解惑(第2页)
第589章找人解惑(第2页)
>
>“思念成疾。昨夜梦见桑吉措站在雪山之巅向我招手,醒来发现枕巾湿透。我不知自己是否还能活着走出高原,但若真有来世,愿做她门前的一棵树,春来开花,冬去守候。”
尼玛次仁的眼泪终于落下,砸在纸页上,晕开了一小片墨迹。她从未想过,自己的血脉竟始于这样一场风雪中的相逢??不是包办婚姻的木牌契约,不是族长手中的签筒,而是一个北京青年和一个草原女子,在天地绝境中彼此照亮的三天。
“你父亲没能完成这份报告。”江慎行轻声道,“他们在返程途中遭遇雪崩,整支队伍被掩埋。三个月后才找到部分遗体,而这批资料,因提前寄出才得以幸存。”
尼玛次仁抬起头,目光如炬:“所以我要替他走完这条路。”
江慎行点头:“我已经联系了自然资源部,他们愿意提供卫星遥感数据支持。但实地勘测必须由专业团队执行,而且……危险系数极高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站起身,走到窗前,“可你知道吗?就在上周,初二班有个女生问我:‘老师,为什么我们只能修房子、种地、当医生?能不能也去挖矿、找石油、建大桥?’我说能。但她接着问:‘那为什么课本里的科学家,全是男人?’”
她转身盯着江慎行:“我不想让她长大后还要问同样的问题。”
三天后,一封署名“措哇女子科技创新实践基地全体师生”的请愿书递交至省教育厅。标题只有八个字:**“女儿亦可探山河”**。
申请内容包括:组建首支全女性高原地质科考队,以“继承先辈遗志,填补祖国地质空白”为目标,启动“林振国计划”??对羌塘北部未知区域开展为期六个月的系统性勘探。
舆论再度沸腾。
有人质疑:“一群小姑娘,连高原反应都没克服过,就想挑战死亡禁区?”
也有支持者发声:“一百年前,女人连学堂都不让进;五十年前,她们还在为识字权抗争。现在,她们要走向地球最深的裂缝,这本身就是文明的进步。”
一个月后,批复下来了。国家地质调查局牵头,联合北大、中科院青藏所,正式立项“青藏高原女性科学力量培育专项”。首批入选队员共七人,平均年龄二十三岁,全部毕业于雪莲未来学院首届工程实验班。
集训在青海格尔木进行。每天清晨五点起床负重跑,下午练习岩芯取样与GPS定位,晚上学习冻土力学与地震波解析。尼玛次仁作为队长,带头完成每一次极限训练。有一次模拟雪崩逃生,她在零下二十度环境中连续匍匐前进两公里,膝盖磨破渗血,却始终没喊停。
出发前夜,卓玛来到营地。
她没说话,只是将一条绛红色的哈达系在尼玛次仁颈间。那是她珍藏多年的圣物,曾挂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前整整一年。
“我不是为你祈福。”她说,“我是提醒你??当你迷失在暴风雪中时,请记住,有一种光,比太阳更早升起,那就是人心底不肯熄灭的信念。”
启程那天,全校师生列队送行。李岩带着学生们搭建了一座临时拱门,用太阳能板拼成“出发”二字,通电后熠熠生辉。江慎行扛着摄像机一路跟拍,镜头扫过每一张年轻的脸庞,最终定格在尼玛次仁背上那只印着校徽的登山包。
车轮碾过积雪,驶向苍茫群山。
接下来的半年,外界几乎失去了她们的消息。仅有几次卫星电话传回简短汇报:
>“已抵达色林错北岸,发现疑似新断裂带迹象。”
>“遭遇强风暴,两名队员轻度冻伤,全员安全。”
>“在海拔五千一百米处采集到古生物化石样本,初步判定为中新世哺乳动物遗骸。”
第七个月初,一则紧急通报震惊全国:科考队所在区域发生里氏5。8级浅源地震,震中正位于其预定勘探路线中心。由于地处无人区,通信中断,救援直升机三次尝试进入均因天气恶劣失败。
全国上下屏息等待。
第十天,一支民间搜救队冒险突入震区,在一处塌陷的冰川谷地中发现了她们的营地残骸。帐篷已被积雪掩埋大半,但外围用石块摆出了巨大的SOS信号。更令人震撼的是,营地中央竖立着一面褪色的红旗,上面用黑色油彩写着一行大字:
**“此处发现铀矿伴生异常,建议列为国家战略储备区!”**